量子纠缠背后的故事(五十)
阿斯佩的实验
克劳泽1969年博士毕业时带着他的帆船回到西海岸,曾顺路到加州理工学院看望他身为著名教授的父亲。欣喜的父亲特意为他牵线搭桥,约好时间去拜见那里更为著名的费曼教授。
忐忑不安的克劳泽来到费曼的办公室,提起他去伯克利后准备进行的实验。费曼一听之下很生气,嚷嚷道:“你这是干什么?你不相信量子力学?等你真找到什么不对的地方再来找我谈。出去吧,我没兴趣。”克劳泽只得悻悻而退。
整整15年后,正忙于巡回讲解新实验结果的阿斯佩也应邀来到加州理工学院。这一次,他得到费曼的欢迎和友好接待。
阿斯佩知道没有人会愿意抢着做他设计的量子纠缠实验,因而他与西蒙尼当初一样不着急,从容不迫地慢工出细活。在1975年面见贝尔得到首肯后,他直到七年后的1982年才发表实验结果。那已经是克劳泽和弗里德曼实验的整整十年之后。好在他的判断无误,没有重蹈西蒙尼被克劳泽抢先的覆辙。
与克劳泽、西蒙尼的CHSH论文一样,阿斯佩很早就以论文的方式发表了自己改进的实验设计。在克劳泽的实验中,钙原子受热激发,通过级联辐射几乎同时产生两颗互相纠缠的光子。它们由光学系统分别导向左右两个方向,通过那里的偏振片测量自旋态。这如同一对双胞胎在光源处相揖而别,分别到左右两个检查站各自接受询问。
每次测量时,克劳泽那左右两边的偏振片有着事先固定好的预设方向。那相当于要询问双胞胎的问题在他们分手时已经锁定。如果双胞胎以某种方式得知他们将要被问到的问题,他们完全有机会互相通气、协调答案。
为防备这样的作弊可能,阿斯佩在每个测量地点装置上两个有着不同预设方向的偏振片。在抵达它们之前,光子先经过一个反应速度非常快的开关,像火车路轨上的道岔一样临时决定让光子去哪一个偏振片。这样,光子在通过开关之前不可能“知道”它会去哪一个偏振片。当它们各自通过开关时,彼此已经相距相当地远,而且即刻便进入偏振片。这时,即使它们有以光速联络的手段也也不再有足够时间协调、作弊。
正是这样一个简单的设计让贝尔、科昂-唐努德日和他们那个日渐扩大的小圈子中所有人激动不已,翘首以待七年之久。
作为研究生,阿斯佩也没有多少资助。他不得不仿效克劳泽的榜样四处搜集、借用他人的仪器设备。克劳泽还越洋过海地给他送来自己使用过的偏振片,并随时为他提供咨询帮助,包括修改论文中的英语。
阿斯佩把他好不容易得到的一笔资金全都用来购置一台强有力的激光器,作为激发原子蒸汽的能源。那是弗里多年前已经在克劳泽实验基础上做出的改进。经过多年的调试,克劳泽当年需要几天的辛苦才能采集到的样本数目在阿斯佩的实验室中几分钟就足以完成。这不仅显著提高实验的效率,也大大增强了数据中的信噪比和可靠性。
1982年7月,他的论文终于在美国的《物理评论快报》上正式发表。伯克利的嬉皮士们早在那半年前就得到了德斯班雅的通报。阿斯佩的实验结果毫无悬念。在杜绝了作弊的可能性后,纠缠中光子对的行为与克劳泽已经证实的完全一致,依然违反着贝尔的不等式。
正如爱因斯坦所担心,量子力学中确确实实地存在有鬼魅般的超距作用。它可以瞬时地协调相距天文距离之遥的两个纠缠中粒子的行为,完全不受光速的限制。这个真实的物理现象彻底违背了传统的局域性因果关系——爱因斯坦心目中所有科学逻辑的能够存在的基石。
1979年初,伯克利那个活跃了四年多的基础物理小组散伙了。卡普拉和祖卡夫因出书而名利双收的意外成功为这小团体带来心理不平衡因素,不再能继续纯真地讨论他们的学术和精神升华。随着年轻学生的陆续毕业,他们各奔东西,为自己的生计和出书计划绞尽脑汁。
但他们依然无法忘怀的是那个实现超光速通讯的梦想。
早在赫伯特之前,小组成员们就已经提出过多种根据贝尔揭示的超距作用实现超光速通讯的可能方式。如若成功,那会是一个颠覆人类思想、改变世界的重大突破。他们一边争取美国国防部、中央情报局以及形形色色的私立企业、富豪资助,一边甚至开始了专利申请的程序。克劳泽的实验已经基本证明了量子纠缠的真实存在,利用其中的超光速联系进行现实的通讯似乎指日可待。
当相距非常远的两颗光子之一因为被测量发生波函数坍缩而进入某一个特定量子态(比如自旋向上)时,与它纠缠着的那另一颗会瞬时地进入与之相对的量子态(自旋向下)。如果那里的人——或某种智慧生物——看到那颗光子波函数突然坍缩为自旋向下,他们可以知道所在遥远的第一颗光子在那一刻经受了那样的测量。这个信息的得来完全不需要时间,超越了光速。
然而,那里的人要“看到”光子波函数的突然坍缩也只能通过实施同样的测量。即使那遥远的第一颗光子并没有被测量,这颗光子在被测量时也会发生波函数坍缩,随机地显示自旋的向上或向下。因此,只是看到光子波函数突然坍缩并不能确定那是来自远方量子纠缠的信息,那也可能还是自己在本地的测量结果。
克劳泽和阿斯佩之所以能够证实量子纠缠的存在,是因为他们是“高高在上”的观察者,可以同时操纵着两颗光子在不同地点的测量方式,然后比较它们的结果。
只在一颗光子所在地点的观察者仅靠自己无法区分远方的消息和本地的坍缩。他们必须事先与对方的测量人员沟通,确定测量的方式方法。然后在事后对照他们的结果。否则,他们所看到的量子态充满了噪音,无法分辨来自远方的信息。显然,他们这样的沟通、对照只能通过电话、电报这一类工具进行,是一个无法超越光速的寻常通讯方式。
伯克利国家实验室的核工程师埃伯哈特(Philippe Eberhard)在1978年发表论文,系统地论证了这个逻辑的瓶颈。他也是基础物理小组的常客,在同伙们的兴致勃勃中保持了清醒的头脑,给他们当头浇下第一盆凉水。量子力学的非局域性并没有违反狭义相对论,超光速通讯仍然是痴心妄想。
赫伯特还是不甘心。他那个利用光子线偏振和圆偏振两个不同量子态进行信息编码的假想试验已经以论文预印本的方式流传甚广。他自信这个别出心裁的精巧设计已经成功地绕开了埃伯哈特发现的局限。但也在那时,远在大西洋彼岸的意大利物理学家吉拉迪(GianCarlo Ghirardi)也对这一问题发生兴趣,在仔细分析赫伯特的论文后找出了他的另一个纰漏。与当时许多类似的设计相同,赫伯特忽视了经典的光束与量子的光子之间的区别。
半波片随圆偏振光转动是一个宏观、经典的过程,可以由麦克斯韦的电磁波理论描述,即光束中携带的角动量传递给了半波片。相对于由几乎无穷多光子组成的光束,单一光子的自旋角动量极其微不足道,无法被半波片察觉。的确,根据量子力学的不确定原理,半波片需要有无穷大的质量才能具备探测到单一光子自旋角动量的灵敏度。当然,质量无穷大的半波片根本不可能被光子或任何力量推动。因此,赫伯特的实验设计压根就无法应用于微观世界中的光子。
1979年11月,吉拉迪和他的合作者里米尼(Alberto Rimini)、韦博(Tullio Weber)也正式发表论文抨击赫伯特的设想。在最后的总结中,他们特意说明如此大张旗鼓是为了重申超光速通讯不可能是最基本的物理规律,要彻底终止这一无谓的争执。
赫伯特没有气馁。他独自冥思苦想不到一年就卷土重来,又提出一个改进版的设计。
问世20年后,激光已经成为物理实验室中常见的仪器。利用爱因斯坦最先提出的受激辐射原理,激光名副其实地是一个“光的放大器”,可以同时产生大量处于同一个量子态的光子,形成完全“相干”(coherent)、整齐如一的激光束。在赫伯特看来,激光器就是他本职工作中日常打交道的复印机,能够将一颗光子“复印”几百万份。这正好能解决半波片无力探测单一光子自旋角动量的难题。
在新版设计中,赫伯特不再直接用偏振片或半波片测量到来的光子,而是将这颗光子引进激光的共振腔,用它作为“原件”复印出几百万颗一模一样的光子。它们形成宏观的激光束,却又都处于与原来光子一模一样的同一量子态。这样,他不再需要担心灵敏度问题。恰恰相反,他有足够的光子可以同时进行多种测量:比如可以将光束等分成两份,分别用偏振片和半波片测量其偏振态。
如果偏振片发现光子自旋向上和向下的数量相同,而半波片也发现光子左旋、右旋的数量等同,那说明到来的那颗光子处于随机的叠加态。它的波函数在自己这边的测量之前没有坍缩过。亦即,遥远的对方尚未进行测量,没有送来信息。
如果偏振片发现光子自旋都是向上,没有向下的。那时半波片依然会报告光子左旋、右旋的数量相等。这个情形说明那颗到来的光子在己方测量前已经处于自旋向上的本征态。那是因为它远方的纠缠同伴已经被用偏振片测量过,那边的光子波函数坍缩为自旋向下,造成这颗光子的自旋向上。
反之,如果偏振片发现光子自旋向上、向下的数量相同,而半波片发现光子都是左旋的,就说明遥远的对方使用了半波片测量,那边的光子进入了右旋的量子态。
如此这般,赫伯特便可以做到在不需要与对方事先通气、事后对比结果的情形下完全获知那一边的测量情形。假如那边的人分别用偏振片、半波片作为“0”、“1”的编码工具,就可以像计算机网络一样传递实用的信息。而这个传递过程没有任何时间延迟,实现了超光速通讯。
赫伯特兴奋地把这个新设计命名为“闪光”(FLASH)。那是“第一个激光放大的超光速连通”1的英文缩写。这一次,他把论文提交给始终关注这个领域的《物理学基础》杂志,并循惯例将预印本在同行中广为寄送。
1981年10月,惠勒携夫人应中国科学院和中国科技大学邀请来到中国访问讲学。那是半个世纪前海森堡、狄拉克、玻尔相继访问中国后西方一流量子力学专家的再次来访。中国业已经历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正处于改革开放之初的百废待兴、朝气蓬勃时期。
惠勒在北京、上海、合肥做了一系列学术讲演,向与世隔绝几十年的中国科学家介绍了现代物理学的新前沿。自然,他也着重讲解了自己提出的“参与式宇宙”概念和“延迟选择”假想试验。
在中国进入“科学的春天”那个年代,玻姆、贝尔、西蒙尼、克劳泽这些长期被忽视的量子力学持不同政见者也终于迎来了他们的量子之春。在维格纳、惠勒、德维特、德斯班雅的不懈推动下,EPR、量子纠缠、贝尔不等式这些非主流概念开始进入常青藤下的象牙之塔,在惠勒的课程和各种学术讲座、会议上登堂入室。越来越多的主流物理学家开始意识到量子物理中的确还存在有根本性的基础问题。
费曼在加州理工学院的同事盖尔曼已经因为发现基本粒子的夸克结构赢得1969年诺贝尔奖。他在那个年代也开始趟入这一谭混水,撰文控诉:毫无疑问,发展量子物理合适的哲学表达被耽误了如此之久,完全是因为玻尔给整整一代的理论物理学家洗了脑2。
作为“觉醒”的新一代,他们与新时代的嬉皮士殊途同归相映成趣。
阿斯佩的实验结果正逢其时,没有再像十年前克劳泽那样只是石沉大海无人问津。
大功告成后,阿斯佩来到旧金山湾区访问度假。克劳泽经常带着他扬帆出海,在加州的蓝天白云下商谈量子力学。他们也热烈地讨论赫伯特的超光速实验提议。虽然都觉得难以置信,他们也想不出辩驳的理由。
但阿斯佩的清净日子没能过多久。他已经因为自己的实验成为一时的学术明星,不断地收到来自世界各地的讲学邀请,包括费曼所在的加州理工学院。
在那里,已经久经沙场在讲台上游刃有余的阿斯佩不慌不忙地侃侃而谈。最后,他提起曾经读到过的一篇论文,其作者似乎在不知情之下独立地推导出了贝尔的不等式。然而,那位作者却无法判定那个奇怪的结论是否说明量子力学存在有麻烦。为此,他在论文中写出了一段弯弯绕绕不知所云的议论。说着,阿斯佩在投影仪上展示出那个作者莫名其妙的话语。然后,他才显示该作者便是在座的费曼。
讲台下的教授们面面相嘘,直到听到费曼自己发笑之后才敢随之哄笑不已。
讲座结束后,费曼热情邀请阿斯佩去继续讨论。在那间克劳泽曾被驱逐的办公室里,两人相谈甚欢。费曼还专门找出自己的论文原稿,证实阿斯佩引用的确实是他的原话。阿斯佩离别后,他又专门去信表达钦佩之意。
费曼自然不是一个“闭嘴”的角色。但他在量子力学中最擅长的还是针对具体问题的计算,曾先后发明了路径积分和费曼图等方法协助、简化计算的步骤。在巴西时,他对玻姆的隐变量尝试丝毫没有兴趣,更觉得艾弗雷特理论中会出现无穷多个大同小异的世界属于荒唐透顶。无怪乎,克劳泽那时也没能得到他的青睐。
但在自己发现类似贝尔不等式的关系之后,费曼对阿斯佩的实验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在那个量子力学的火热年代,他意识到量子世界与经典世界有着本质性的不同。两者之间存在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对此,费曼也找出了一个独特的视角。
(待续)
First Laser-Amplified Superluminal Hookup
The fact that an adequate philosophical presentation has been so long delayed is no doubt caused by the fact that Niels Bohr brainwashed a whole generation of theorist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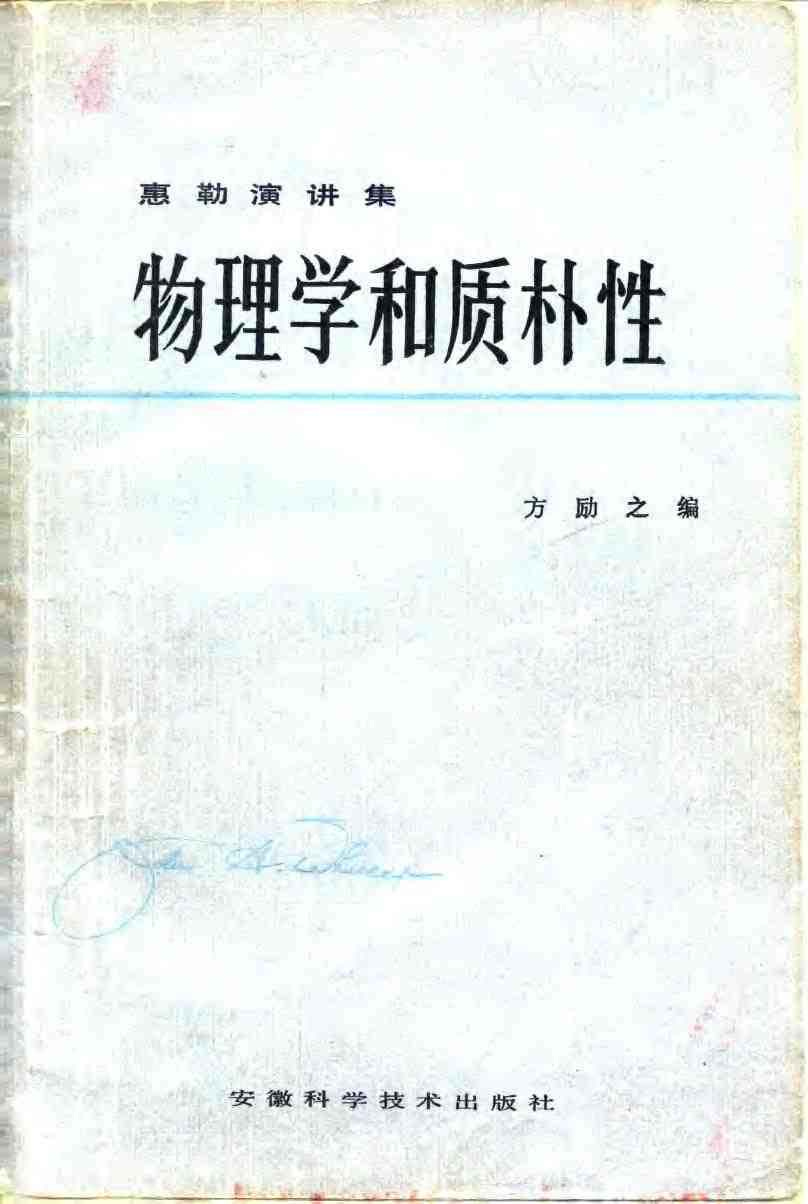
不在科学网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