量子纠缠背后的故事(卌八)
意识的力量
1969年,由植物学家莱茵在杜克大学创建,已经有12年历史的超心理学会(Para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被美国科学促进会(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接纳为会员,进入美国的科学大家庭。
作为科学促进会理事会成员,物理学家惠勒投了反对票。他认为这个致力于鼓吹“超感官知觉”特异功能的学科是伪科学或至少非科学,不具备与美国物理学会、美国心理学会等200多个科学组织平起平坐的资格。
惠勒在理事会中只是少数派。那时候,他也还不知道自己捅的是一个什么样的马蜂窝。
1972年9月,26岁的以色列青年盖勒(Uri Geller)受邀访问旧金山附近的斯坦福研究所(Stanford Research Institute)。这个研究所原来隶属于当地的斯坦福大学,是二战、冷战时期美国军方在大学中设立的众多研究机构之一。1960年代以来,大学生出于对军队势力急剧膨胀和越南战争旷日持久的不满发动校园抗议,迫使斯坦福大学与这个研究所解除了关系。研究所遂成为独立的私营机构,依然在国防部资助下从事军事科研。
进入1970年代时,二战之后的世界格局大势已定。美国和苏联两个超级大国都已拥有原子弹、氢弹和导弹、航天技术,进入势均力敌的对峙状态。“缓和”(detente)逐渐取代两败俱伤的军备竞赛。相应地,美国政府大举削减国防经费,原本轰轰烈烈的军事科技突然资金紧缩。行业中一下子变得有闲无钱的大量技术人员只好另谋出路。
斯坦福研究所的两位物理学家别出心裁地从一位富商那里争取到一笔资金,开始他们的超感官知觉研究。盖勒是他们的主要实验样本。他在以色列已经小有名气,不仅精通读心术和心灵感应,还能凭自己的意念将汤勺、钥匙之类的金属物弯折。斯坦福研究所的人员专门设计各种实验手段测试他的超常技能,确认了真实性。他们意图窥觑其背后的秘密,发掘人类自身中还隐藏着的潜在能力。
这个项目在研究所内名叫“psi实验室”(psi lab)。那是超心理学的常用英文缩写,源自希腊语中“意识”一词的第一个字母Ψ,也是英语“心理学”(psychology)和其它含义相近词汇共同词根的来源。当物理学家涉足这个领域时,他们自然地注意到Ψ也是薛定谔当年为他那含义不明波函数选取的数学符号,业已成为量子力学的象征。
无怪乎荣格和泡利曾确信心理学与量子物理之间存在有神秘的“共时性”联系。
1960年代的美国经历了剧烈的社会动荡。在世界大战胜利后成长的新一代不再认同战后经济扩张的繁荣昌盛和社会稳定。他们更注目于国内黑人争取平等的民权运动和国外深陷泥潭的越南战争所暴露的矛盾和动乱。为逃避对现实的失望和未来的迷茫,他们急流勇退,投身于以性解放、吸毒和摇滚乐为号召的“嬉皮士”(hippie)热潮。西海岸的旧金山正是这一运动的中心。在神魂颠倒的迷幻药和动人心魄的摇滚乐刺激下,他们可以暂时性地离开身边的物质世界进入超脱的精神乐园。
身居象牙塔内的青年物理学家也不例外。他们在战后拥有的天之骄子地位几乎一夜间消失殆尽。迫于越战压力,美国政府改变政策,征兵时不再照顾有学问的大学生、研究生。几年前还被视为国家宝贵战略资产的物理学子们与社会青年同样地面对远赴越南战场卖命的威胁。
即使幸运地躲过了征兵抽签,他们的前景也不容乐观。逐年扩充的物理专业在1970年达到顶峰。那年美国培养出超过1500名的物理博士,创历史最高纪录1。同时,冷战的降温导致国防、工业界对物理人才的需求一落千丈。大学里本来不多的教职也已人满为患,能出现的空缺凤毛麟角。
于是,他们同样地陷入迷惑和颓废,寻求思想逃避的世外桃源。特异功能、鬼魅般的超距作用……这些非主流概念正好可以填补他们的精神空缺。当年,泡利和约旦都曾将超感官知觉与量子力学中的纠缠相联系。后来的维格纳还进一步添砖加瓦:在“维格纳的朋友”中,波函数Ψ的坍缩及物理现实都会取决于作为个体的每个人的不同意识。人类的精神意识不再只是心理学的概念。它是物理世界的一部分,更可以通过引发波函数的坍缩直接改变这个世界的进程。这一切也正好与那时随嬉皮士运动而流行的“新时代”(New Age)思维完美契合。
在普林斯顿,维格纳和惠勒都已进入老一代物理学家的行列。在冷战时期,两人都坚持保守的政治立场,为美国核武器发展竭尽全力。他们因而在思想左倾的大学校园内成为不为人理解的异端,倒也彼此惺惺相惜友情倍增。
在学术上,惠勒在战后专注于被物理学界遗忘的广义相对论,以他“一切都是场”的理念理解这个世界。1960年代初,宇宙微波背景辐射的发现证实了勒梅特、伽莫夫提出的设想:宇宙起源于一次“大爆炸”,其后处于不断的膨胀之中。2至少在那个高能的早期宇宙,量子力学是世界演化的主导甚至唯一方式。
当年在与学生米斯纳和艾弗雷特一起探讨时,惠勒就意识到那时的宇宙不存在任何有意识的观察者。艾弗雷特因而提出他的多世界诠释,取代依赖于观察者的哥本哈根正统理论。随着宇宙学的突破,艾弗雷特将整个宇宙看作一个量子系统的观点在1970年代不再是天方夜谭。他的理论也因为德维特的推介更广为人知。但他的导师却还是没能接受那个出格的思想。
作为玻尔的忠实学生,惠勒始终坚持哥本哈根的正统,其中观察者与被观察的现实不可分割。早在40年前,约旦曾不容置疑地宣布,“是我们自己制造出测量的结果”,“一个现象只有在成为被观察到的现象之后才成其为实在的现象”。他所谓的“我们”便是后来由维格纳阐明的有思想意识的生命体。
惠勒认为那是经典物理与量子物理之间的本质区别。他亲手绘制了一幅漫画表现这个不同。在牛顿的经典世界中,观察者隔着一块厚重的玻璃在观察另一边的世界。这个观察者自己超脱于那个世界之外,世界的演化不会因为他的观察而改变。但在量子的世界里,那块隔离的玻璃被粉碎,观察者的手伸进了世界之中。他在观察的同时也在挪动着那个世界的林林总总。观察本身在“制造”观察的结果。没有观察,就不会有客观的实在。
他把这个量子的世界称之为“参与式宇宙”(participatory universe)。观察者本身就在宇宙之中。
我们之所以知道有一个早期的宇宙存在,是因为我们今天观察到宇宙背景辐射,从中获取了那个客观世界的信息。但惠勒还更进一步。他指出这样的观察同时也是宇宙当初发生演变的缘由:我们今天的参与式观察触发了早期宇宙波函数的坍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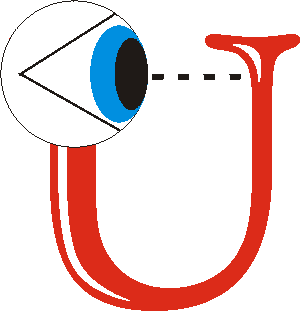
他也绘制了一幅展示这个关联的漫画。在他简洁的图像中,过去与现在、实在与意识、主观与客观,相辅相成对立统一地构造出浑然一体的怪圈。
克劳泽在1969年来到的伯克利已经不是奥本海默、玻姆20年前书生意气的那个小镇。经过麦卡锡主义的洗礼,那些曾风行一时的左派共产主义团体烟消云散,硕果仅存者也都转入地下苟延残喘。取而代之的是校园内外的政治抗议和嬉皮士的狂欢,延续着年轻人反抗主流的叛逆精神。
邻近斯坦福研究所的特异功能实验也激励了伯克利的青年。这里的两个物理研究生在1975年发起一个名为“基础物理小组”(Fundamental Fysiks Group)3的社团,吸引了十来位本校物理系学生、研究生和青年教师,还有附近闻风而来的国家实验室、企业研究机构的年轻人。他们属于被“闭嘴、计算”抛弃的新一代,正前途未卜。同时,他们也已经对那个传统的研究方式深恶痛绝,渴望对量子力学有自己创新性的深层理解。
他们每星期定时聚会、讨论。在斯坦福的实验之外,身边的克劳泽也自然地成为关注对象。在这个无拘无束的小团体中,克劳泽意外地找到他在正统学术界遍寻不得的知音。
最令他们感兴趣的自然是盖勒如何以意念掰弯金属勺子,或推而广之,人类的意识如何才能改变物质的世界。为此,他们集中探讨如何为意识构造出物理模型。
在这群少不更事的嬉皮士之中,稍为年长的赫伯特(Nick Herbert)成为一个领头人。他已经在1967年获得斯坦福大学的物理博士,毕业后一直在附近的企业工作,研发新材料和通讯工具,尤其是当时最先进的打印、复印、传真技术。利用职务的方便,他大量复印自己找来的非主流物理论文与小组成员分享。
也是出于职业习惯,赫伯特尤其关心人类是否、如何能够通过物理仪器交流意识。与斯坦福研究所类似,他请来各路神人,让他们对一些仪器施展功力,试图在连接着的打印机、传真机上记录他们的意识流。甚至,他认为这样可以时光超越,接收到已经去世的古人发来的信号。
他的现场演示——往往伴随着足够的啤酒和大麻——每次都会成为基础物理小组聚会的高潮节目。
克劳泽在这么一群既桀骜不羁又玩世不恭的嬉皮士中如鱼得水。同时他也理智地调侃这些人不过精神不正常的“疯子”(nuts)。本质上,他自己还是一个在实验室中兢兢业业探索的“正经”物理学家。
在伯克利的国家实验室,克劳泽还有一位前辈支持者。斯塔普(Henry Stapp)1958年时就已经在伯克利获得了物理博士学位,其后远赴苏黎士担任泡利的助手。那年泡利意外辞世,他又去慕尼黑师从海森堡。受泡利的影响,他对人类意识在量子力学中扮演的关键角色无法忘怀。他毫不吝啬地夸赞贝尔不等式是历史上“最深刻的科学发现”4。
虽然他那时已经年近半百,斯塔普也是基础物理小组的骨干成员。
盖勒在斯坦福成功后名声大噪,一跃而成国际明星。玻姆也慕名邀请他前往伦敦访问,亲自测试他的超常能力。美国国防部和中央情报局等部门皆闻风而动,为这个新科技注入大量资金。斯坦福研究所自然也获益匪浅。如果心灵感应、意念移物可以成为现实,其价值无可估量。
虽然斯坦福研究所的实验远比莱茵当年所作精密、全面,他们还是遭到行家的质疑。他们最大的缺陷在于对自己的科学、技术能力过于自信,没有专门邀请职业魔术师协助把关。其实,特异功能的表演在历史上并不鲜见,也非常容易令人信服。往往只有魔术师才能以他们专业的眼光识破表演者的暗中手法,破解其骗局。
轰动一时的特异功能那时也已经引起了科学界和魔术界的警觉。他们联手成立了一个“超自然声称科学调查委员会”(Committee for the Scientific Investigation of Claims of the Paranormal),专门揭露其中的造假行为。委员会成员、著名魔术师兰迪(James Randi)应邀来到斯坦福研究所协助分析盖勒的实验。果然,兰迪很容易地以魔术手法“重复”出盖勒的特异功能,让那里的科学家灰头土脸。
但这并未妨碍盖勒继续他的明星生涯。
其实,在主流物理学界的眼里,贝尔、克劳泽、西蒙尼那批人也不过几个与嬉皮士大同小异的疯子,徒劳地挑战着坚不可摧的量子力学正统。尽管有维格纳、德斯班雅的努力,他们依然是物理学的边缘人。
曾经发现电子自旋,又在战场上捕获海森堡等德国物理精英的古德斯密特在战后长期担任美国《物理评论》和《物理评论快报》的主编。仗着十多年的编辑经验,他在1973年撰文提醒,物理学是一门实验科学。如果不能与实验数据相联系,物理理论完全没有意义。因此,他禁止在这些刊物上发表纯粹“哲学性”讨论的论文。
这基本上杜绝了讨论量子力学基础问题的可能。只有像克劳泽、西蒙尼的CHSH论文、克劳泽和弗里德曼的实验结果因为讨论的是具体的实验才能过关。克劳泽一针见血地指出,假如古德斯密特的新政出现在40年前,玻尔那篇回应EPR的论文就不得出笼。
那还是没有互联网的时代,他们不得不另谋出路。那年年底,瑞士一家基金会资助创立一份《认识论快报》(Epistemological Letters),为他们提供了一席之地。那其实很难说是一份期刊杂志。它只是由手工打字、滚筒油印,然后简单装订的通讯。
这个直接冠着“哲学性”名称的不起眼通讯拥有一个后来声名显赫的作者群。德布罗意、维格纳、贝尔、德斯班雅、克劳泽、西蒙尼、斯塔普、霍恩、泽赫等人都曾在那上面奋笔疾书,展开激烈的辩论。西蒙尼还担任了编辑。在那些粗糙油印的页面里,量子纠缠的早期理论逐渐成形。
借用那个年代的时髦用语,克劳泽亲切地将这个“地下刊物”称之为“量子亚文化”(quantum subculture)。那是他们一小撮持不同政见者抱团取暖的窝棚。
1976年4月,贝尔和德斯班雅在意大利西西里岛上的埃里斯举办了一个会议。这次会议纪念的是费米当年的学生马约拉纳(Ettore Majorana)5。
那是这群边缘人物六年前在科莫湖欢聚一堂之后的又一次盛会。贝尔已经成为他们的领袖,而克劳泽是会议理所当然的新星。还在为找工作焦头烂额的克劳泽起初不敢保证他能有时间去意大利。贝尔不得不发紧急电报祈求:“如果没有你,这个会议就只是一幕没有王子的《哈姆雷特》。”克劳泽阅后欣然赴会。
在他的主题演讲中,贝尔系统地回顾了这些年的进展,包括克劳泽、弗里等人的实验成果。经过几年的摸索、核实,他们已经基本能够确信纠缠中的光子对会表现出违反贝尔不等式的行为,因而存在有鬼魅般的超距作用。但贝尔强调,更引人注目的将会是阿斯佩那个还处于策划过程中的实验设计。他期待也相信阿斯佩的新实验能够在不久的将来关闭现有实验中的漏洞,杜绝光子对作弊的可能性,为爱因斯坦的疑惑奠定最终的结论。
身为研究生的阿斯佩第一次参加这样的会议。他在会上报告了实验的设计,很诧异地发现自己已经成为众望所归的对象。会后,一位与会者介绍他认识了偶像科昂-唐努德日。出乎阿斯佩的意料,正在成为法国量子力学最高权威的科昂-唐努德日没有指责阿斯佩的离经叛道,反而对他激励有加。在接下来的几年里,科昂-唐努德日常常走访阿斯佩的实验室,近距离地关注他的进展。
正牌大师的亲身支持改变了阿斯佩在实验室同行们眼中的形象。他不再只是一个自不量力的疯子。至少在巴黎郊区的那个实验室里,量子纠缠的实验也不再被视为毫无意义的无事生非。
(待续)
这个记录直到最近的2008年后才被再度超越。
其中“物理”一词的拼写来自作为玻尔母语的丹麦语。
the most profound discovery of science
马约拉纳才华出众,但年仅32岁即在西西里乘船时失踪。他曾预测存在一种反粒子就是其自身的粒子,即“马约拉纳费米子”。




量子物理不需要玄学化。观察者要用某种能量波同被观察物质的波反应才能产生数据,被观察波的能量因此集中在一点两点或几个点,有几率没有我们了解的运作方程式,就像原子波函数从一个态转去另一个态吸收或放射量子,有几率没有我们懂的运作方程式。这些同那些古古怪怪的理论,uri geller 的变魔术,毫无关系。
物理学究们这么容易走偏门,是这个时代的文化趋向一部分,把 feeling 放在 reasoning 之上。记者们去请教披头士列侬如果得到世界和平,跟你去粉川普希望他拯救美国,都是感性超出理性的例子。也就是科学破除迷信几百年后,美国社会觉得科学太难懒得学,要人力就去印度进口,把工厂送给中国,自己多搞些虚无的投资产品,加密货币,空壳公司值几百亿,同一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