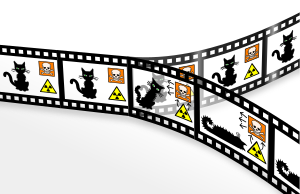量子纠缠背后的故事(四十)
艾弗雷特的世界
爱因斯坦去世半年后,玻尔迎来了他的70大寿。
即使还是爱因斯坦在世的年月里,玻尔在物理学界内部的声望也已超越了爱因斯坦。从哥本哈根研究所出来的一批又一批精英,如同当初伯克利的奥本海默和这时普林斯顿的惠勒,正在世界各地扎根发芽开花结果,培养出一代又一代的追随者。他们像自己的导师一样视玻尔为至高无上的“教父”。在相对论淡出视野、量子理论成为物理学主战场的20世纪,年轻人眼里的爱因斯坦、薛定谔、德布罗意乃至狄拉克都不过是远离物理主流的古董。只有玻尔老当益壮,依然在前沿指点江山运筹帷幄。
在为玻尔祝寿的文章中,海森堡第一次正式提出“哥本哈根诠释”这个一锤定音的名称。作为国际知名的一流科学家,海森堡在战争结束后没有遭遇太多麻烦。他很快定居于玻恩不得不逃离的哥廷根,与劳厄等人一起重建德国的物理研究。适时地高举以玻尔为首的哥本哈根大旗显然对他个人形象的重建也大有益处。1
在大寿的几年前,玻尔已经得到丹麦新国王授予代表国家最高荣誉的“大象勋章”(Order of the Elephant)。依照传统,他为自己设计了一枚贵族纹章。在大象勋章缎带和坠饰的环绕中,纹章的主题是源自中国的阴阳太极图,辅以拉丁文箴言:“对立即互补”。
在玻尔深邃的目光里,当初为解释量子力学之诡异而总结出的互补原理并不局限于物理。他很早就指出生物在整体上有着自主的目的性,而组成生物体的分子却只遵从机械的物理定律。与光的粒子、波动性质一样,这二者互相冲突、不可协调,在理解生物行为时又缺一不可。那便是互补原理在生物学中的体现。
在心理学中,他看到理智和情感的互补。在人类学、社会学……,玻尔发现对立而又互补的关系无处不在。他相信这是他发现的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哲学、方法论,比他在原子、原子核模型上的贡献有着更为深远的意义。为此,他不遗余力地四处宣讲推销,确立自己的历史地位。
也是到了1950年代中期,惠勒才得以在普林斯顿重新安顿下来,专心研究自己钟情的学术。那时他周围的世界和他自己的兴趣都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研制原子弹是美国物理学界在战争期间同仇敌忾的努力。但原子弹在日本使用所造成的巨大伤亡也让他们中的大多数不堪回首。战争结束后,他们回到各自安静的书桌,不愿意继续染指大规模杀伤武器。惠勒成为屈指可数的例外之一。他依然无法忘怀弟弟那一句绝望的“快点!”,唯恐美国会落在苏联后面导致悲剧重演。不顾同事、朋友们的反对,他追随泰勒和极少数志同道合者重返洛斯阿拉莫斯基地研制威力更为强大的氢弹。2经过三年奋战,他们在1953年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氢弹。
怀着那强烈的爱国主义情绪,惠勒没有加入对他曾经面试过的玻姆被停职和解雇、奥本海默接触机密资格被取消的同情、抗议行列。
还在投身氢弹研究之前,惠勒还曾提出一个新的原子核模型,弥补液滴模型的简陋不足。他自然地将论文初稿寄给导师玻尔审阅。玻尔读后非常热情,立即入伙合作。当然,那接下来便是典型玻尔式的无休止讨论和修改,一下子竟拖了三年多。直到玻尔表示自己退出后,惠勒才和他的研究生自行发表了论文。然而为时已晚,哥伦比亚大学的雷恩沃特(James Rainwater)提出了同样的模型并率先发表,随即由玻尔的第四个儿子奥格(Aage Bohr)和莫特森(Ben Mottelson)在哥本哈根证实。他们三人后来以此成就获得1975年的诺贝尔奖。
失去先机的惠勒对玻尔没有丝毫抱怨,反而对导师更为敬重。3他只是得到了一个深刻的教训:有了新成果应该尽快发表。
因为身在普林斯顿,惠勒在二战后的中坚一代物理学家中逐渐成为一个绝无仅有的异数:他同时与玻尔和爱因斯坦两位大师保持着极为融洽的师生、同事乃至朋友关系。在爱因斯坦的耳濡目染下,惠勒的学术观点有了一个180度大拐弯。
在费曼发明粒子运动的路径积分、玻姆复活粒子的确定轨迹之际,惠勒反其道而行之,
抛弃原来“一切都是粒子”的理念,转变为“一切都是场”(everything is fields)。那正是爱因斯坦毕生坚持但壮志未酬的信念,也成为年轻惠勒的志向。为了完成统一场论,惠勒提出一个同时具备引力和电磁力的“几何子”(geon)概念。随着兴趣的转向,他连年自愿在普林斯顿开课讲授那时已经近乎无人问津的广义相对论,以便自己能掌握这一陌生的学问。
借近水楼台之利,惠勒每学期都会请爱因斯坦前来客串一堂课,为年老的大师和青年的学生提供难得的零距离接触机会。爱因斯坦人生最后一次讲课便是他去世一年前在惠勒为研究生开设的相对论课上。不过,他们的话题却很快转往量子力学。当学生们复述着从惠勒那里学到的测量理论时,爱因斯坦慈祥地问道:如果是一只老鼠在观察,也会改变宇宙的状态么?
那堂课上有一个刚入学的研究生艾弗雷特(Hugh Everett)。与其他同学一样,这是他第一次与爱因斯坦面对面。但这却不是他们的第一次打交道。11年前,还只12岁的艾弗雷特曾给爱因斯坦写信,声称他解决了一个无解的问题:当一个不可阻挡的力量冲向一个不可移动的物体时会是怎样的结局?爱因斯坦和蔼地回信,解释真实世界里不存在不可阻挡的力量或不可移动的物体,有着的却是一个成功地克服了自己为此特意构造的困难的倔强男孩。
各式各样的矛盾、悖论是艾弗雷特自小就心驰神往的乐趣。在天主教大学学习期间,他撰写了一篇证明上帝不可能存在的论文,以无懈可击的逻辑让那里的教授为之癫狂。来到普林斯顿后,他的兴趣也集中在隔壁的数学系。那里的专家们正在热火朝天地发展冯·诺伊曼早年创始的博弈论(game theory),正合艾弗雷特的口味。他因此有了毕业后将博弈理论运用到军事战略上的志向。
爱因斯坦对量子力学测量理论的批评立刻吸引了艾弗雷特的注意力:那也是一个似乎无解的悖论。他暂时从数学的博弈中脱身,回到物理系对付这个难题。自然地,他选择惠勒作为博士导师。与玻尔一样,惠勒时常鼓励研究生要敢于挑战权威,打破沙锅问到底。
于是,艾弗雷特找来冯·诺伊曼和玻姆的教科书,开始自己寻根问底。他终于领悟了爱因斯坦的那句发问背后的睿智。在冯·诺依曼总结的哥本哈根诠释中,如果没有人类的测量活动,量子力学便无从谈起。与爱因斯坦一样,艾弗雷特觉得这不可思议。物理学的对象应该是一个独立于人类主观行为的客观实在。
冯·诺伊曼将量子力学分成两个截然不同的过程:在没有人测量的时候,量子系统的波函数遵从薛定谔方程——或者推广后的狄拉克方程——演变。那是一个连续、平滑、确定的过程。而当测量发生时,处于叠加态的波函数会突然坍缩到其中一个本征态。那是一个断裂、突然、随机的过程,不仅不符合薛定谔方程,而且完全没有任何数学或逻辑的描述。那其实只是玻尔和冯·诺伊曼等人空口白话的断言。
最让艾弗雷特不安的还是这个测量过程需要明确地区分观测者和被观测的对象。玻尔认定观测者属于经典的宏观世界,被观测的是微观的量子世界,二者泾渭分明。这个论断在薛定谔以他那戈德堡机器将微观的放射性原子与宏观的猫纠缠在一起后已然站不住脚。艾弗雷特认同玻姆的看法:微观和宏观世界遵从着相同的物理规律,是一样的量子世界。
但这样一来,当某个人在实施观测时,世界会骤然分成两部分:整个世界都是量子的集合,只有观测者自己单独地“清醒”着,君临天下般观察那个世界并造成其波函数的坍缩。在艾弗雷特看来,这无异于哲学上的“唯我主义”(solipsism):只有自己是实在的,其它所有一切不过是虚幻。
这在科学上很难站得住脚。无怪乎爱因斯坦会发问,如果那观测者是一只老鼠,也会是一样的情形吗?
艾弗雷特意识到这是量子力学中最基本的矛盾,只有彻底颠覆哥本哈根诠释才能破解这个他平生所遇最为蹊跷的悖论:客观世界中没有观测者与被观测系统的区分,也不存在波函数坍缩这么一个没有任何逻辑推理、证据支持的先验概念。
薛定谔的戈德堡机器将他那箱子里的放射性原子、盖革计数器、毒药瓶、锤子和猫纠缠在一起,成为同一波函数描述的量子系统。在箱子被打开之前,它们的共同波函数遵从他的方程连续、平滑地演变。只是在箱子外的人打开箱子往里看时才发生突然的坍缩。那箱子之外是一个与箱子内部完全不同的经典世界:观测者。
艾弗雷特认为那也是一个既没有根据也没有必要的分野。箱子本身不过是一层隔板,箱子内的猫和箱子外的人同样可以在电磁相互作用下纠缠在一起,属于同一个量子系统。人打开箱子的过程也不过是它们共有波函数演变的一部分。因为不再有外在的观测者,这个波函数的演变完全由薛定谔方程描述,不会有莫名其妙的坍缩。
推而广之,艾弗雷特提出整个宇宙都处于一个统一的“宇宙波函数”(universal wavefunction)之中。这个波函数时时刻刻、永永远远地遵从薛定谔方程连续、平滑地演变,不会发生坍缩。
来得早不如来得巧。惠勒那时也正同另一位研究生、艾弗雷特的好朋友和室友米斯纳(Charles Misner)一起兴趣盎然地研究广义相对论,希望能采用费曼的路径积分将这个被遗忘的经典理论量子化。他们很快遇到一个大问题:如果整个时空宇宙是一个量子系统,那怎么可能会有外在的观测者?更何况相对于宇宙的存在,能够实施测量的人类甚至老鼠都还只是最近才出现的角色。
艾弗雷特的宇宙波函数来得正是时候。惠勒在阅读了他严密的数学推导后大为倾服,觉得这可能是实现量子引力理论的有效工具。然而,他同时也为艾弗雷特为新理论提供的物理诠释忐忑不安。
当宇宙波函数完全遵从薛定谔方程演变时,量子的世界与牛顿的经典世界一样是完全确定的,不再具备随机因素:上帝果然不会掷骰子。也许爱因斯坦的在天之灵会为之欣慰,艾弗雷特却还必须解释实际观察中诸如放射性原子衰变、自发辐射那些现实的随机性事件。
他找出了一个听起来惊世骇俗的机制。
处于叠加态中的波函数随时间演变时并不一定总是保持其整体性,也可以依照内含的本征态“分叉”,各行其是地继续演变。当波函数描述的是整个世界时,这意味着世界也随之分裂,变成多个互为独立的世界。每个世界的波函数只是原来叠加态中的本征态之一。在某些世界里,人们会看到某个原子发生了衰变、某个原子自发地发出了辐射;另一些世界中,人们看到的却正好相反。这些观察的结果取决于该世界所拥有的本征态,而这些世界出现的可能性取决于该本征态在叠加态中所占的成分。
这样,在薛定谔的假想试验中,世界便是在箱子被打开的那瞬间一分为二。在其中的一个世界中,人们看到箱子里发生了原子衰变,毒药瓶已经被打碎,猫死去了。另一个世界中,人们却发现箱子里一切完好如初,啥事没发生过。
乍听之下,这个世界性的分裂似乎比波函数坍缩更为突兀甚至恐怖。但这个过程却是波函数连续演化的自然状态,不具备任何突然的变动。世界中的人类、生物不会察觉它的发生。分裂之后的不同世界各自为政,之间无法互通信息也不可能知道对方的存在。对艾弗雷特来说,最关键是这个过程不依赖于测量的发生、观测者的存在,也就不需要人为地区分量子与经典的范畴。量子的世界——或者说整个的世界——都完全是一个独立于人类主观行为的客观实在。
美国著名诗人弗罗斯特(Robert Frost)在《未选择的道路》4中感慨,在森林中遇到岔路时,只能选择其中一条走下去,无法同时领略另一条路的风光。在他所知的经典世界里,只存在一个选择而无从两全其美。
在哥本哈根的量子世界里,弗罗斯特似乎可以同时走上两条路。但那却只是一个幻觉。当有外人事后窥视,发现他的行踪时就会发现他其实只走了其中的一条。
而在艾弗雷特的世界中,弗罗斯特的的确确地同时走了那两条路。那时已经有了两个弗罗斯特,他们分别在不同的世界中走上了不同的路——与薛定谔的猫无异。只是那两个弗罗斯特彼此永久分离,还是无法知道另一个世界中的自己在那不同的路径上获得的感受。他们浑然不知对方的存在。
当惠勒看到艾弗雷特把宇宙比作能够随时自主地一分为二的单细胞变形虫(amoeba)时不禁毛骨悚然。但更让他不寒而栗的是这个新思想与他奉之为真的哥本哈根诠释格格不入。即使是极力鼓励学生大胆创新并及时发表新成果的惠勒也不敢贸然造次。依照早已养成的习惯,他把艾弗雷特论文初稿寄给玻尔,请他先行审阅、定夺。在信中,惠勒小心翼翼地反复表明这篇题为《没有随机性的波动力学》5只是一个不成熟的看法,还有待大幅度地修改。
普林斯顿虽然有着惠勒在仿照玻尔模式建立他的哥本哈根,爱因斯坦的影响却挥之不去。从费曼到玻姆到艾弗雷特,那里的年轻人似乎一直在离经叛道。玻尔毫无悬念地拒绝了艾弗雷特的提议。哥本哈根大本营里的年轻助手们更为激烈。他们指责艾弗雷特的多此一举不过是因为他没能理解量子力学的测量理论,盲目挑战一个完全没有问题的既定之规。借在欧洲访问的机会,惠勒亲赴哥本哈根,希望至少能说服他们接受宇宙波函数的概念,也只是功败垂成。
无奈,惠勒回到普林斯顿后与艾弗雷特开夜车反复改写论文。在惠勒的指导、坚持下,艾弗雷特舍弃了变形虫的形象比喻,大刀阔斧地删去几乎全部的诠释性文字,只保留了惠勒欣赏的宇宙波函数概念和相应的数学推导。修改后的论文不再强调世界的分裂,只是提出一种逻辑的可能。
艾弗雷特还按照惠勒的建议将他的理论命名为《量子力学的“相对态”表述》6:一个不至于令人惊诧的平淡题目。惠勒依然不放心,他又自己写了一篇附录式的论文,为艾弗雷特的新理论提供自己的解释。至此,惠勒至少已经说服他自己艾弗雷特的新思想其实与哥本哈根诠释并不矛盾。
1957年1月,美国的一群物理学家在北卡罗来纳大学所在的教堂山召开会议讨论广义相对论。惠勒再次成为组织者,带去了米斯纳等一班学生,还邀请了过去的学生费曼。在那次会议上,费曼提出“粘珠论”,指明探测引力波的实际可能性。7
艾弗雷特没有赴会。因为他的宇宙波函数对惠勒的引力研究至关重要,惠勒带着他们的论文在会上散发,也引起了与会者的讨论。
几年前对玻姆的隐变量兴趣缺缺的费曼对宇宙波函数也同样地嗤之以鼻。8他指出这样的宇宙波函数必须包含着宇宙演化历史中出现的每一个可能性之两面,因而会同时存在着无穷多个同样现实的世界。在费曼看来,这是一个概念性的困难。
也是会议组织者的德维特(Bryce DeWitt)负有为会议编辑论文集,作为专刊在《现代物理评论》杂志上发表的重任。他满怀好奇地仔细研读了艾弗雷特的论文,发现他既欣赏这一新思想又无法接受。因为宇宙的不断分裂会出现越来越多的世界,他把艾弗雷特的理论命名为“多世界诠释”(many-worlds interpretation),将他和惠勒的附属论文一起收进了这个广义相对论的论文集。
之后,德维特意犹未尽。他又给艾弗雷特写了一封长信,不断夸赞艾弗雷特独创的思维和严谨的逻辑,同时也频频提出各种质疑。最后,他机智地提醒艾弗雷特:我本人就从来没有感觉到过自己突然分裂成两个自我。
艾弗雷特接到这个对他论文绝无仅有的正面回应后回了一个简短的答复。他告诉德维特他读到的只是一个被惠勒残忍阉割过的版本,完全丧失了他的物理思想。在对他的新诠释稍作解释后,艾弗雷特反过来提醒德维特:当年在伽利略时代,人们也曾如此反驳地球绕太阳公转的谬论:他们从来没有感觉到过自己脚底下地球的运动。
德维特阅后凛然一惊。
(待续)
战后出现的第一本原子弹通俗历史是瑞士一位记者根据海森堡一面之词写作的《比一千个太阳还亮》(Brighter than a Thousand Suns)。玻尔读后十分愤怒,写了一封信驳斥。但玻尔没有寄出或公开那封信,直到他去世后多年才被发现。因为保密要求,在战俘营中掌握了海森堡真实情况的古德斯密特也不便出面揭露。
为了劝说反对核武器的费曼加入,惠勒预测下一次世界大战有40%的可能会在几个月内打响。那也是费曼远避到巴西的原因之一。
这也是一次历史的重复:玻尔年轻时曾因为恩师卢瑟福的缘故没能发表他的同位素论文,错过一次诺贝尔化学奖的机会。
The Road Not Taken
Wave Mechanics without Probability
"Relative State" Formulation of Quantum Mechanics
详见《捕捉引力波背后的故事(之二):费曼的机灵和罗森的固执》
费曼也没有看上导师惠勒的“几何子”理论。在那次会上,他恶作剧地将惠勒的名字John改成发音相近的Ge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