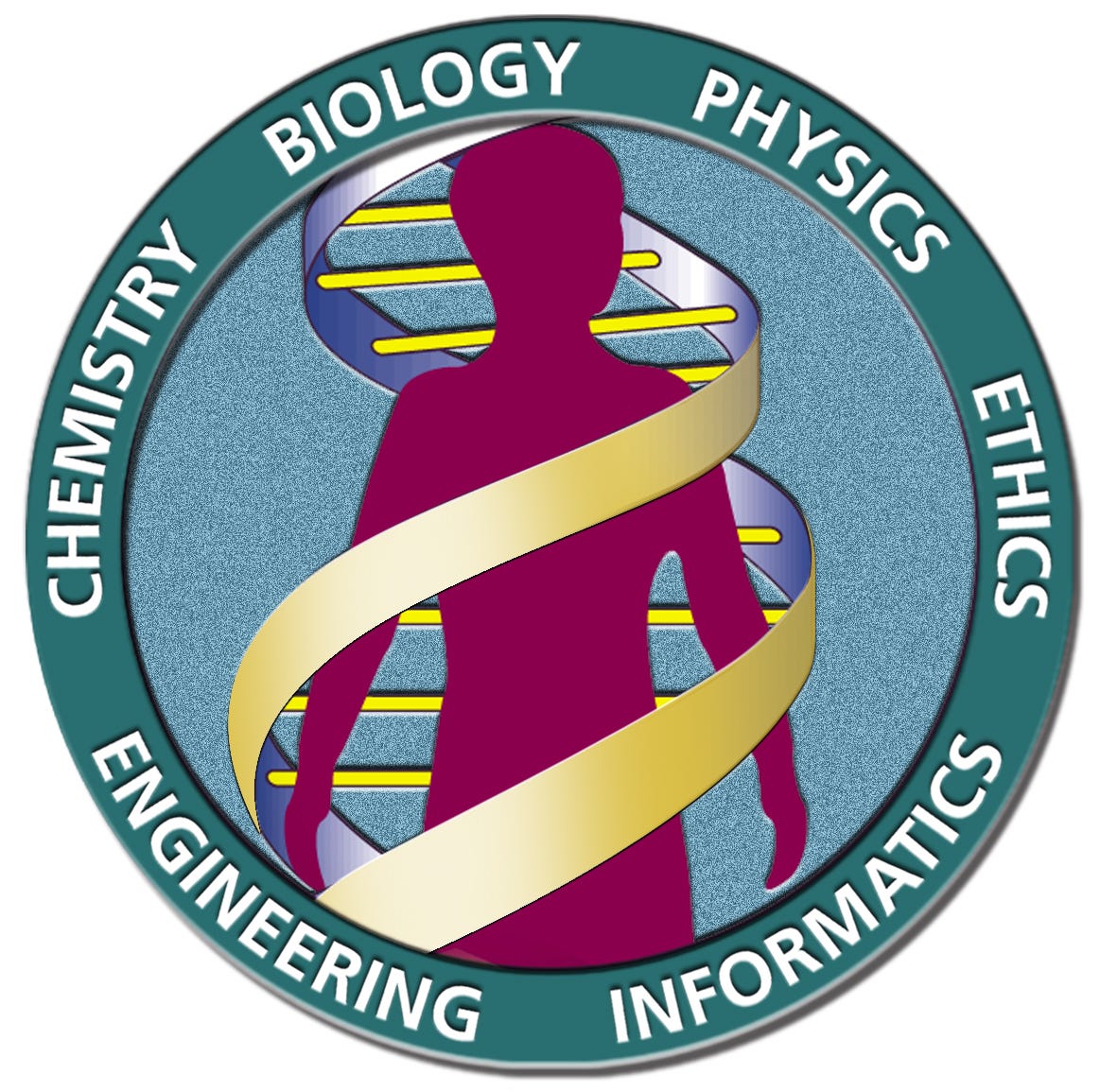生命编码背后的故事(卌八)
人类基因
作为冷泉港会议的组织者和东道主,沃森甚少在会议上现身。他没有参与围绕为人类基因组测序工程的激烈争执。即使偶尔在会场露面时,他也显得心不在焉。只有最亲近的朋友知道沃森的心事。会议开幕前夕,沃森年仅16岁的儿子私自从精神病院里脱逃,下落不明。
虽然风流倜傥,且身为举世皆知的青年才俊,沃森在情感生活上屡战屡败,1直到面临不惑的39岁时才与一位年方19的大学生步入婚姻殿堂。他们很快有了两个儿子,但大儿子年纪轻轻即被诊断患有精神分裂症,曾在半年前试图跳楼自杀。沃森不得不将他送进全封闭管理的精神病院。
所幸的是儿子很快被找到,安全地送回精神病院。只是沃森随后也不能再专心于会议事务。儿子的命运是他的心病。与鲍林同样,沃森觉得精神分裂症是一种与镰状细胞贫血症类似的先天“分子病”,根源在于儿子身体内的基因和突变。只有全面掌握、理解人类的基因信息,才有可能以现代分子生物学研究人类自身,真正地理解儿子的不幸。虽然没能参与会议的争辩,沃森对人类基因组工程有着更为深切的使命感和紧迫感。
一个月后,沃森、吉尔伯特和布伦纳等人来到美国首都华盛顿参加又一个人类基因组测序讨论会。这次会议在国立卫生研究院内举行。那是政府资助医学、生物学研究的主力机构。不过会议的实际主办者却是一个私立的基金会:霍华德·休斯医学研究所2。
休斯(Howard Hughes)是美国的传奇人物。他在20世纪初投身好莱坞,从事电影导演和制作。同时,他又精于设计、制造飞机,经常冒险试飞自己新创的机型。这两大实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和前后均取得辉煌成功,将他推上首屈一指的富翁宝座。为了逃避高额的所得税,休斯在1953年底捐出大笔资产设立公益性的医学研究所,以资助与医学有关的基础科学研究、为人类造福为主旨。凭借雄厚的财力,这个新兴研究所很快取代更为传统的洛克菲勒基金会成为支持美国医学研究最为强有力的私人财源。
休斯研究所成立那年正逢沃森和克里克发现DNA双螺旋结构的轰动。他们立即将遗传学定为最为关注的前沿。休斯在1976年去世后,继承其遗产的研究所更是如虎添翼。虽然属于私营基金会,研究所采取与作为政府机构的国立卫生研究院携手合作的方针,几乎不分彼此地共同推进美国的医学研究。在1986年的夏天,他们也都在积极探索为人类基因组测序的大业。
那次会议后不久,沃森他们又得到美国科学院的国家科学研究委员会3征召。那里也在为人类基因组测序项目进行专家评议。
经过这些旷日持久的讨论研究,能源部、休斯研究所和国立卫生研究院、科学院分别达成大同小异的共识。人类基因组的测序将是一个庞大又极具意义的项目,在科学价值上足以与登月、航天甚至建造原子弹比肩。那时正引领风骚的航天飞机每发射一次就消耗4.7亿美元。为人类基因组测序的30亿美元不过相当于航天飞机的六次发射,显然是一笔超值的买卖。
同时,他们也充分认识到生物学家在冷泉港会议上提出的诸多异议,认为一蹴而就地展开人类基因组测序的条件尚未成熟。三个部门不约而同地提出应该将整个项目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暂时不进行测序,集中人力物力测定人类染色体中各个基因相对位置的“遗传连锁图”(genetic linkage map)。那正是斯图尔特文等人在1910年代为果蝇染色体所做的基因位置图,也是韦克斯勒和金分别搜寻亨廷顿病和乳腺癌基因的主要手段。一个完整的人类遗传连锁图可以大大缩减调查类似遗传病所需的时间和努力。相对于果蝇的四对染色体,人类23对染色体宛如浩瀚大海,即使在70多年后也还未能形成完整的领航图。借助RFLP分子标记新技术和政府大规模拨款的支持,人类染色体遗传图谱的完成将为寻找致病基因提供比人类基因组全部碱基序列更为直接、及时的帮助。当然,他们也将在这个第一阶段中注重基因测序和数据存储、处理等相应技术的开发,为下一步全面测序打好基础。
这个第一阶段估计需要五六年的时间。届时,生物学家可以对人类基因组有更直接、深入的认识。他们将能够通过技术发展的评估再决定是否开启下一阶段的全面测序。那时,他们还可以从酵母菌、线虫、果蝇、老鼠等生物学家已经非常熟悉的简单生物开始,积累经验后再进军人类的基因组。
无疑,这是一个脚踏实地按部就班,同时也注重实用价值的计划。
吉尔伯特最先失去了耐心。在他看来,这几个机构反复扯皮的结果是在为人类基因组测序的使命前畏缩不前,宏大的目标一再被降级和推迟,在可见的未来还是遥遥无期。1987年2月,吉尔伯特向国家科学研究委员会告辞,宣布自己将创办一个“基因组公司”4,以独立自主的私营企业方式投入基因大潮。
那时的吉尔伯特刚刚经受人生第一次创业失败,被迫离开渤健公司返回学术界。但他的创业精神依然故我,时刻都在寻找新机会。他看出基因测序即将成为一个巨大的产业。仅仅十来年前,从事核酸实验的研究生都必须学会分离、纯化实验用的限制性核酸内切酶。然而这门手艺很快“失传”:1970年代后期的研究生可以方便地在市场上订购这种酶,不再需要亲自动手。这如同他们早已无须学习如何吹制实验所需玻璃器皿的技能。吉尔伯特预见正在分子生物学实验室中热火朝天的基因测序也会很快地走上同一条路径。他的基因组公司可以抢先占据市场,在基因测序上承担起类似制作玻璃器皿或分离限制性核酸内切酶的服务。这样,生物实验室和商业公司的科研人员可以将基因测序的简单劳动“外包”5给他这个更为专业化、效率也就更高的基因组公司。他们互惠互利。科研人员从繁复操作中获得解放,专心于自己更有价值的科研课题。基因组公司也能从中收费获利。
当然吉尔伯特的志向并非只是创办一个科技服务公司。在为他人做嫁衣裳同时,他将利用公司规模可观的设备和专业人员率先展开人类基因组的测序。作为商业行为,他们将拥有自己新测定碱基序列的知识产权,以专利或版权方式予以保护。其它实验室和公司需要向基因组公司付费才能获取使用权。对人类基因的认识已经开始在防病治病和制药等方面崭露头角,其潜在市场无可估量。
这是一个相当超前的眼光。
早在1790年,赢得独立战争仅七年、正在创建一个崭新国度的美利坚合众国通过专利法,保障新技术发明者的商业利益。经过近两个世纪的实践,专利在20世纪的美国有着明文规定的保护范围:在“方法”(method)、“机器”(machine)、“制造产品”(article of manufacture)和“合成材料”(composition of matter)中的创新。当西拉德在1953年提醒沃森考虑为新发现的DNA双螺旋结构申请专利时,他们都随即打消了这个念头。DNA的双螺旋是自然的产物。虽然属于新发现,它与专利法里那四个以英文字母“M”打头的范畴毫不相干。
伯耶和斯旺森的基因泰克公司首先在1982年独树一帜,为他们的胰岛素生产赢得专利权。胰岛素也是天然的分子。基因泰克通过基因重组方式生产的胰岛素与自然的胰岛素没有实质区别,并不属于新“产品”或“材料”。他们因而将胰岛素的人工生产作为新“方法”获得批准。那是基因产业的第一个专利,在为基因泰克带来巨额利润的同时也为生物科技革命拉开序幕。
在那六年后,伯耶和科恩的基因重组“方法”专利才获得批准。科恩所在的斯坦福大学拥有这个专利的主要所有权。作为非营利的公益组织,他们没有锱铢必较,慷慨地允许大学、研究所等同类非营利机构免费使用这个分子生物学实验室里不可或缺的技术,只向财大气粗的商业公司收取使用费。纵然如此,斯坦福大学和伯耶所在的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也从中获得高达2.5亿美元的收益。
DNA中的碱基序列不是人为的“产品”或“材料”,为它们测序也不涉及新的“方法”。在吉尔伯特雄心勃勃的1987年,囊性纤维化、亨廷顿病、乳腺癌等致病基因尚未见踪影,为测序而得的基因信息申请专利还属于天方夜谭。但吉尔伯特的远见已经触发沃森的警觉。与吉尔伯特看到潜在巨额利润相反,沃森担忧的是专利对科技进步形成的障碍。
穆利斯那个属于鲸鱼公司的聚合酶链反应专利也在1987年获得批准。这个大大加快基因测序的手法同样在分子生物学实验室中必不可少。然而,鲸鱼公司以及随后高价从他们手中购得该专利的大公司都没有沿袭斯坦福大学的策略。他们为这个专利使用权定下高价,无论商业公司还是科研单位都必须付费才能使用。在沃森的冷泉港实验室,他们以教育目的为中小学生制作的简便DNA实验器具因为采用了PCR技术也必须向大公司缴纳高达15%的使用费。
假如吉尔伯特的计划成为现实,对人类健康、生命至关重要的基因信息有可能尽数成为私人财产,为学术界和医药领域的科研带来额外负担,违背治病救人、为人类造福的初衷。沃森等生物学家于是有了时不我待的急切。他们公开呼吁必须抢在吉尔伯特和其它私营公司之前完成人类基因组的测序。人类的生命编码应该属于全人类,作为“公有领域”(public domain)的知识资产无偿共享。
沃森等人的大声疾呼给予吉尔伯特为创办新公司的筹资运作致命一击。老奸巨猾的风险投资业本来已经因为吉尔伯特在渤健公司的败绩踌躇。假如有着政府投资作后盾的科学界果然捷足先登,将所有基因信息无偿公开,他们大赌注的投资只有血本无归的下场。那年10月,美国的股票市场发生大崩盘,风险投资业更是雪上加霜。吉尔伯特不得不偃旗息鼓,放弃他的基因组公司美梦。还要再等六年多之后,他才通过创办麦利亚德公司在乳腺癌筛查中拔得头筹,终于品尝到创业成功的喜悦。
吉尔伯特堪称为人类基因组测序最为热心的吹鼓手。但他的离去也没有影响国家科学研究委员会的定夺。在委员会的推荐下,美国科学院在1987年正式发表报告,支持国会以专项拨款的方式资助这个极有意义的项目。他们建议的资助额为每年二亿美元,以15年为期,总额正是吉尔伯特估算的30亿美元。报告同时也指出这么一个大项目应该有统一的领导机构,摒弃那时能源部与国立卫生研究院各行其是的混乱。但纵使科学院也不愿意得罪政府部门。他们未对那两大门户直接评判,只将这个烫手山芋扔给国会。
作为美国学术界最高权威的代表,科学院的报告为拨款法案在国会的通过起了很大的推进作用。而在能源部和国立卫生研究院互不相让的争相游说下,国会也没有在二者中做出选择。于是,两个名为“人类基因组计划”(Human Genome Project)的新机关分别在能源部和国立卫生研究院内同时出现,呈分庭抗礼之势。因为先声夺人,又挟持着由核武器基地转型为国家实验室的人力物力和技术储备,能源部赢得国会拨款中的大份额。视生物学为独家手艺的国立卫生研究院自然不甘示弱。他们祭出一个独特的撒手锏:聘请沃森作为己方的人类基因组计划负责人。
沃森那时已经58岁,年近花甲。他在冷泉港实验室乐不思蜀,并不情愿再度投身江湖。但为人类基因组测序的潜在价值让他激动不已。在那些年没完没了的会议中,沃森一再强调这个大科学项目必须有一位出类拔萃的领导者。这个人选既必须是生物学内行,又要能在议员、政客以及学校、研究所、基金会的各类人物中游刃有余,还应该是一名为公众所熟知的人物。唯有如此,才能持续保持纳税人的支持,保证项目的后续资金和平稳运行。虽然他竭力故作隐晦,所有人都清楚他所描述的条件鲜有人能满足,实属为沃森自己量身定制。
克里克早在1976年离开剑桥,同时也离开了他近乎一手开创的分子生物学。与德尔布吕克十多年前离开噬菌体领域相似,克里克在奠定遗传的分子理论之后功成身退,华丽大转身地投入一个冷门的新前沿:大脑、神经和意识。沃森于是成为DNA双螺旋结构独占鳌头的代表人物。他已经在冷泉港实验室担任20多年的主任,锤炼出扎实的科研管理和筹款能力。在诺贝尔奖获得者的光环下,他更因为《双螺旋》一书的流行和争议在知识界家喻户晓。即使没有他跃跃欲试的自荐,沃森作为人类基因组计划的领袖也实属众望所归。
在随后提交给冷泉港实验室的报告中,沃森解释道,“我只可能有一次这样的机会,让我的科学生涯涵盖从双螺旋到人类基因组中30亿个阶梯的历程。”630年前,他和克里克发现DNA双螺旋长链之间有着以碱基对构成的一个个阶梯,正是薛定谔所谓储存着生命编码的“非周期性晶体”。通过人类基因组计划的实施,沃森又有机会近距离看清那一个又一个的阶梯本身,读出其中的每一个字母。那30亿个阶梯或字母应该蕴藏着人类生命的全部秘密、生老病死的旷古之谜。假如读懂这部天书,他也期望着终于能从中获取对自己大儿子不幸命运的彻底理解。
这是沃森不能错过的人生契机。但他也还舍不得离开冷泉港。经过一番讨价还价,他得到两全其美的安排,同时在冷泉港和国立卫生研究院身兼二职。他的出场果然不同凡响,立即聚集起新闻界的镁光灯。国立卫生研究院的人类基因组计划即刻被推向最前台,成为事实上的领导者。财力、人力雄厚的能源部不得不退居二线。
为了消除同行们的顾虑,沃森坚持他的人类基因组计划是一个只在名义上隶属于国立卫生研究院的独立机构。两者的预算完全分开,保证人类基因组计划不至于蚕食甚至鲸吞生物学界已有的“正常”科研资金。经过一年多的积极游说和筹资,沃森的队伍急剧膨胀。他的小机构升级为“国家人类基因组研究中心”7,坐拥6千万美元的年度预算。那已经是能源部相应部门的两倍之多。他还自作主张,规定将预算的百分之三专门用于研究与基因组、基因信息相关的伦理、法律和社会影响问题。这个份额随后又增加到百分之五,其目的在于为人类接受、理解即将到来的自身基因信息做好思想准备,避免重复传统优生学和纳粹种族灭绝那样的历史悲剧。
一切就绪后,沃森郑重其事地宣布人类基因组计划在1990年10月1日正式启动。那是美国政府部门新财政年度的开始日期。
那一天,生物学走进了大科学时代。
(待续)
沃森2002年出版自传《基因、女孩和伽莫夫:双螺旋之后》(Genes, Girls, and Gamow: After the Double Helix)作为《双螺旋》的续集,不厌其烦地详尽叙述自己年轻时追求女孩的执着和挫伤。
Howard Hughes Medical Institute
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
Genome Corporation
outsourcing
I would only once have the opportunity to let my scientific career encompass a path from the double helix to the three billion steps of the human genome.
National Center for Human Genome Researc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