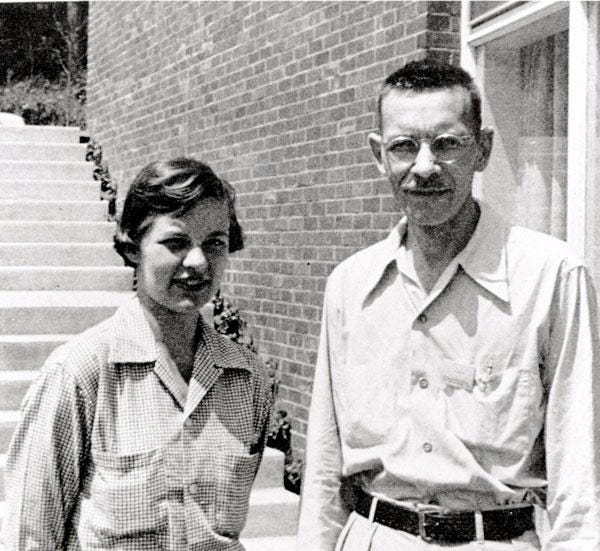生命编码背后的故事(三十)
大胆假设
在国王学院,威尔金斯一放下话筒就在实验室里四处奔走。他们呕心沥血好几年的DNA分子结构被卡文迪许实验室破解的消息无异于晴天霹雳。不一会,威尔金斯给克里克回电话说他会乘坐第二天一早的火车到剑桥。同来的还会有罗茜。
1951年11月27日上午,威尔金斯带着富兰克林、高斯林和另两位同事出现在克里克和沃森的小办公室里。佩鲁茨代表实验室欢迎来客,礼貌地寒暄几句后便抽身离去,将舞台让给这天的明星。克里克早已打好腹稿,准备洋洋洒洒地系统介绍他们的思考和模型。正当他神采飞扬的高嗓门开始在室内回荡时,富兰克林却在一旁看着简陋的模型笑出声来。她不客气地打断克里克的话头,有条不紊地数落起这个模型的荒唐之处。
克里克和沃森用来为三条长链“搭桥”的金属离子在DNA的化学分析实验中从来没有出现过。即使它们可能含量极少尚未被发现,这模型里带正电的离子会吸引容易极化的水分子。离子因而会被小巧的水分子包围、屏蔽,压根无法再吸引带负电的磷酸。这样的三螺旋无法稳定,只会自我分崩离析。
富兰克林在国王学院的那次讲座中曾强调DNA很容易吸收、失去水分,说明其中带负电的磷酸应该处于分子的外围。克里克和沃森的模型偏偏反其道而行之,将磷酸长链深藏在分子中心,被脱氧核糖和碱基分子包围得几乎“水泄不通”。如同一件里外穿反了的衣服1,它无法解释DNA分子吸水、脱水时在A和B两个形态之间的演变。当富兰克林进一步估计这个密不透风的模型中能容纳得下多少个水分子时,沃森才猛然醒悟他那天在火车上凭记忆提供给克里克的数字比富兰克林当天讲授的小了整整十倍!
在去牛津的火车上,克里克正是根据沃森这一数据推断DNA的分子结构不存在太多的可能性,可以逐一排查。如果DNA分子可以吸收十倍的水分,其内部空间必然很大,不同分子结构的可能性也就大大增加。那正是威尔金斯和富兰克林都一再坚持“随意”构造DNA分子模型时机尚未成熟的主要原因。
两拨人马都曾计划在剑桥用一整天的时间研讨这个模型和下一步的计划。但在看了模型,吃过一顿沉默的午餐后,他们已经无话可谈。威尔金斯带着他的人匆匆道别,赶上午后的火车回伦敦,只留下克里克和沃森面面相嘘。他们花了一个星期大胆假设的模型没待小心求证就已经被罗茜驳得体无完肤。
沃森自然懊恼无比。克里克也意识到DNA的吸水量其实是一个化学常识。他在火车上时过于激动性急,竟没能意识到沃森的随口胡诌毫无道理。
几天后,克里克收到威尔金斯寄来的一封正式打字的公函,转告国王学院的一致意见:卡文迪许实验室不应该再继续研究DNA。威尔金斯特地表明该信副本已转交兰德尔,也让克里克与他那边的布拉格分享。随后,威尔金斯又另外给克里克手写一封私信,以朋友的口吻抱怨局面已经不可收拾。他竭尽了全力才避免兰德尔直接向布拉格发难。
因为没有语言障碍,沃森到英国后如鱼得水,与在哥本哈根时的苦闷不可同日而语。但作为美国小青年,他也经常对英国特有的绅士传统不以为然。到来之初,他花了很多功夫说服克里克DNA是比蛋白质更为重要的生物分子。但克里克依然犹豫不决。只因为DNA是国王学院的地盘,卡文迪许实验室不便插手。沃森无法理解英国人在争先恐后的科学发现中也会坚持礼让风格。
布拉格父子之间、伯纳尔和阿斯特伯里师兄弟之间都曾在X射线衍射实验中分别有过君子协定。他们各自循规蹈矩避免直接竞争。克里克最终是在为威尔金斯设置的“鸿门宴”上取得对方首肯后才打消心理顾虑涉足DNA。但他们那个雕虫小技在各自的老板眼中显然不值一哂。
没有人知道兰德尔在逼迫威尔金斯寄送公函之后是否还曾直接给布拉格打电话抱怨,但布拉格也早已火冒三丈。克里克和沃森的恣意妄为不仅有违君子风度,也让实验室得罪在科研经费上举足轻重的医学研究委员会。为保证好钢用在刀刃上,医学研究委员会不允许其资助的机构在同一个课题上重复研究。卡文迪许实验室和国王学院都是委员会资助的大户,各自术有专攻。两个愣头青这个祸闯得着实不小。
暴怒之下,布拉格指令佩鲁茨转告肯德鲁,再由肯德鲁转告克里克和沃森,卡文迪许实验室必须停止一切有关DNA的研究,已有的原子模型等工具一并交付国王学院,作为双方媾和的奉献。倒是肯德鲁有点于心不忍,私下安慰两位年轻人:布拉格能命令他们停止工作,却无法禁止他们在脑子里继续思考DNA。
布拉格还是在同僚的劝慰下才打消将克里克逐出实验室的念头。他退而求其次,要求这位已经蹉跎多年的老研究生专心蛋白质结构,尽快完成博士论文好体面地离开。沃森是远来的客人,布拉格本来对他无计可施。但资助沃森的基金会也恰在那时察觉到沃森和他导师卢里亚的谎言,责成沃森立即回到他学习生物化学的初衷。借助基金会的压力,布拉格安排沃森开展烟草花叶病毒的生物化学研究,以远离DNA。沃森倒是暗自窃喜。只有他知道病毒中最重要的成分不是蛋白质,正是核酸。借着研究烟草花叶病毒的机会,他大量阅读有关文献,补充自己缺乏的基础知识,同时在脑子里继续思考DNA。
在那一番喧闹之中,1951年终于落下帷幕。作为圣诞节礼物,克里克送给沃森一本自己题字签名的《化学键的本质》。也许这本化学大师的巨著还会为他们指点迷津。
开春之后,牛津大学在1952年4月举行微生物学术会议,邀请卢里亚从美国来做报告。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身为敌侨的卢里亚和德尔布吕克都已经归化为美国公民,但卢里亚却在申请护照时被拒,无法出境。沃森只好挺身而出,在会议上宣读导师准备好的讲稿。
卢里亚在报告中总结已经有十多年历史的噬菌体研究,指出这种病毒体内的蛋白质是遗传信息的载体。它们“噬食”细菌时,其蛋白质进入细菌的细胞,产生自己的下一代。沃森原汁原味地朗读后,忍不住自己加上一点私货。他告诉听众最新的实验结果与他刚刚照本宣科的内容正好相反。
噬菌体早已在安德森的电子显微镜中暴露真身。它们的外形像蝌蚪,有一个方方正正的“脑袋”和一条细长的“尾巴”。但相比于单细胞的细菌,噬菌体极其微小,只是比较大的分子,自身不具生命特征。十来年后,电子显微镜的分辨率有了长足的进步。安德森可以清楚地看到噬菌体尾巴的末端还长有更细的触角。病毒与细菌相遇时,这些触角与细菌的细胞膜结合,将病毒固定地依附在细胞外表。安德森还能看出如此一段时间之后,仍然留在细胞外面的病毒发生了变化。它们的“脑袋”变得比较透明,显得空空如也。原来存在于“脑袋”中的物质已经通过尾巴进入细胞,彻底改变细菌的命运。
虽然不是生物专业出身,安德森常年参与噬菌体组的活动后也已经触类旁通。他知道格里菲斯和艾弗里曾将来自光滑肺炎球菌的DNA与无害的粗糙肺炎细菌混合,将其“转化”为剧毒的光滑肺炎球菌。安德森因而认为噬菌体与细菌的关系与艾弗里的转化因子实验异曲同工。是病毒“脑袋”里的DNA进入细菌的细胞,致使该细胞产生数以百计的噬菌体后代。而遗留在外的是病毒的蛋白质外壳。其任务只是为DNA提供保护并在与细胞接触后充当“注射器”,让自己的DNA穿过细胞膜进入细胞2。
当然仅凭电子显微镜的观察,安德森没法确定进入细胞内部的是DNA还是蛋白质。德尔布吕克、卢里亚和他们的噬菌体组都与鲍林一样坚信蛋白质才是生命信息的载体,小小的DNA分子最多不过在起着某种辅助作用。艾弗里的转化因子实验一直没能得到公认,也是因为人们怀疑实验中的高纯度DNA可能还是混有蛋白质成分。
沃森在哥本哈根时曾与马洛一起用放射性同位素追踪噬菌体的DNA分子在遗传中的足迹。德尔布吕克虽然推荐了他的论文,还依然坚持其证据不充分。但在一年后,当沃森宣读导师的论文时,他已经收到赫尔希来信通报最新的发现。作为噬菌体组三巨头之一,赫尔希同样相信着蛋白质的主导地位。他意图用实验一劳永逸地终结来自DNA的挑战。
被德尔布吕克称为“与社会格格不入”的赫尔希以孤僻著名。曾有人想参观他在冷泉港实验室的仪器设备,他不屑一顾地回绝:“我们用我们的头脑工作。”3他这个新实验中最关键的仪器其实就是一个厨房中常见的食品搅拌机4。把布满细菌和噬菌体的培养液放进搅拌机里大力粉碎,就能将紧紧地依附在细胞膜上的噬菌体外壳剥离开来。再用离心机高速旋转,质量相差悬殊的细菌与噬菌体就能完全被分离。
在冷泉港,赫尔希和他的助手蔡斯(Martha Chase)也像沃森和马洛一样用磷的放射性同位素标定噬菌体的DNA。在让它们侵蚀大肠杆菌之后,赫尔希和蔡斯用搅拌机、离心机分离出细菌,结果在细菌中探测到放射性。正如安德森、沃森所料,噬菌体的DNA确实进入了细菌的细胞。
接下来,他们用硫的放射性同位素代替日常的硫原子养殖噬菌体。硫只在蛋白质中存在,其放射性便是噬菌体蛋白质的示踪信号。重复同样的实验后,他们却发现细菌中完全没有放射性。这个结果大出赫尔希之所料,无可辩驳地证明进入细菌的只是噬菌体的DNA,没有蛋白质。DNA在细胞中彻底改变大肠杆菌的生命走向,完全不需要蛋白质的参与。
这个80来年前由米歇尔从脓血绷带中分离出来的核酸分子才是生命奥秘之所在。
牛津会议三个月后,赫尔希在法国巴黎郊区举行的噬菌体会议上正式报告这一成果,顿时引起全场轰动。最引人注目的是鲍林从听众席中站起身,当场承认这个实验让他信服DNA才是遗传的主体分子。生命现象应该就是DNA在指导细胞如何制造蛋白质。
鲍林终于觉察到自己多年的盲点。而他能够出席那次会议却也实属不易。
自从与艾娃结婚成家,鲍林得以全身心投入他的科学事业。艾娃相夫教子,独力承担家里家外全部事务,保证丈夫心无旁骛。即使在家的时候,鲍林除了吃饭睡觉,几乎总是一个人关在书房里阅读、撰写论文。他的几个孩子很难有机会与父亲共处,年幼时经常会趴在书房门外以偷听他用录音机口授文件的声音来体会父亲的存在。多年来,鲍林保持着超常的论文发表速度,成就卓著。但他这个两耳不闻窗外事的平静生活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遭遇挑战。
鲍林在战争之初进入不惑之年。因为严重的肾炎,他几乎英年早逝,只是在卧床半年和艾娃遵医嘱严格控制饮食的悉心照顾下才逐渐恢复健康。那时美国正式参战,鲍林也带着科里和实验室人员全力投入军事性研究。他们研制火箭燃料、合成人造血浆和对付传染病的人造抗体。但当老朋友、美国建造原子弹计划负责人奥本海默(Robert Oppenheimer)来邀请他出任该计划化学部负责人时,鲍林却没有接受。
奥本海默和鲍林都是早年在欧洲学习量子力学的美国青年。鲍林在访问哥廷根时与在那里师从玻恩攻读博士学位的奥本海默相识。5但他们还是学成归国,成为加州理工学院年轻教授后才真正开始兄弟般的友情。那时两人踌躇满志,计划结合各自物理和化学专长研究量子力学中的化学键。比鲍林年轻三岁的奥本海默总是刻意模仿鲍林的做派,还经常送他各种礼物和自己写的诗。因为鲍林喜欢戴一顶小礼帽,奥本海默也帽不离身,后来竟成为他自己的标牌。但有一天,奥本海默单独邀约艾娃一同去墨西哥游玩,被艾娃拒绝。鲍林随即断绝了与奥本海默的来往,也只好单枪匹马挑战化学键的量子力学理论。多年后,艾娃才醒悟奥本海默那时所爱的不是她自己,其实是她的丈夫鲍林。
鲍林觉得自己在加州理工学院的实验室里能更有成效地为战争服务,也不愿意屈居奥本海默之下。他因此没有参加研制原子弹。在那个反法西斯的战争岁月,鲍林并不反对建造和使用原子弹。但在战争结束、世界进入核武器威胁下的冷战格局时,鲍林清醒地意识到新时代的危机。他加入爱因斯坦、玻尔和西拉德等物理学家的行列,联络、组织科学家向公众普及核武器知识和与之俱来的危险。
艾娃也是在那时走出家庭,积极参与社区的志愿活动。她在战争期间亲眼目睹身边日本裔和德国裔敌侨蒙受歧视,乃至被送往集中营,切身感受到社会的不公正。在艾娃的带动和鼓励下,鲍林也与当地的左派和共产主义组织接触频繁,在反对继续研制核武器、推动社会公平等问题上找到共同立场。他们的言论、活动引起广泛关注。那正是以联邦参议员麦卡锡(Joseph McCarthy)为标志的“麦卡锡主义”年代。鲍林因而不得不接受联邦和加利福尼亚州各级机构的调查和讯问,反复表白自己并非共产主义者。1951年4月1日,美国联邦众议院“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6将鲍林列为积极参与“解除美国武装并击败美国活动”7的著名人士之一。
那也正是鲍林和科里完成他们关于蛋白质α螺旋和β折叠一系列学术论文的时刻。政治风波没能影响鲍林在学术领域的披荆斩棘。在蛋白质分子结构中获得突破后,他也把眼光投向核酸。虽然DNA在他心目中并不重要,这个小而简单的分子也可以作为他那“大胆假设小心求证”方法的又一应用。在那个1951年之夏,鲍林先后给国王学院的威尔金斯和兰德尔去信索取DNA的X射线衍射照片和数据。但两人都客气地拒绝,声称他们在公开发表之前需要给自己一点研究的时间。鲍林不以为意,遂暂时将DNA搁置一旁。他已经收到再次前往英国的邀请,蛋白质依然是他需要关注的主题。
鲍林三年前去英国讲学时,蛋白质的分子结构还隐藏在人类观察微观生命的盲区。时过境迁,阿斯特伯里计划在1952年5月1日举行英国王家学会特别会议,专门探讨蛋白质结构在鲍林模型之后遗留的问题。鲍林和科里正忙于拍摄更多的肌肉、胶原蛋白X射线衍射照片,为会议做准备。
那年一月,鲍林向外交部申请护照延期,表明他将去英国、法国和西班牙的大学访问,出席国际学术会议并接受一项名誉学位。2月14日情人节那天,他的申请被拒绝。外交部主管护照的负责人直言相告,他的出国旅行不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
在麦卡锡主义横行的年代,像卢里亚那样因为思想左倾、同情共产主义的学者、艺术家被拒发护照而不得出境已经屡见不鲜。在其后几个月里,鲍林不得不提供证明材料,接受面试,甚至直接求助于曾为他颁发“总统功勋奖章”8的杜鲁门(Harry Truman)总统。这一切都无法改变外交部的决定。政府部门的大胆假设当然无须小心求证。
当王家学会的会议如期召开时,仍然困在美国的鲍林只好请一位同事上台朗读他准备好的演讲稿。没有了大师的风范,那次演讲只收获稀稀落落的礼貌性掌声。
但鲍林的遭遇在会议之外引发轩然大波。英国著名科学家和新闻媒体口诛笔伐,矛头直指美国外交部。法国科学家干脆选举鲍林担任他们即将在巴黎召开的生物化学大会的名誉主席。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外交部长只好出马斡旋,在鲍林宣誓他从来不曾是共产党组织成员后发给他一本时效有限、只允许他出访英国和法国的特别护照。
已经错过英国会议的鲍林直接赶往巴黎参加由他担任名誉主席的生物化学会议,受到英雄般欢迎。他随后又来到近郊的噬菌体会议,万分意外地听到赫尔希证明DNA才是生命遗传信息的载体。
结束在法国的访问后,鲍林再次来到英国。布拉格不可思议地得知鲍林在卡文迪许实验室最想见面的竟是差点被他开除的克里克。鲍林对克里克的螺旋分子X射线衍射理论很感兴趣,热情邀请他获得博士学位后到加州理工学院进修。向来能说会道的克里克在偶像面前罕见地变得谦虚谨慎。他试探地问起鲍林是否考虑过蛋白质的α螺旋可能会互相纠缠。鲍林简单地回了句“我想过”,立刻就转移了话题。
虽然英国学者对鲍林无法出席王家学会的会议深表震惊和同情,他们在那次会议上还是对他的蛋白质分子模型各种不足之处毫不留情。最让他们放心不下的莫过于鲍林的α螺旋有着0.54纳米的周期性,与阿斯特伯里等人实际测量的0.51纳米不尽相符。被布拉格画地为牢后,克里克一直在琢磨这个差异。他想到如果两根或更多的α螺旋非常接近,像弹簧似的交错在一起,单个螺旋的0.54纳米周期性会被彼此掩盖,而出现那个0.51纳米的周期性。鲍林那一句“我想过”让克里克非常后悔自己的冒昧。他随后迫不及待地抢先在《自然》杂志发表快讯,描述蛋白质这个“卷曲螺旋”(coiled coil)三级结构。鲍林回美国后也立即寄出同样内容的论文。这一次,克里克和鲍林同意那是各自的独立发现,避免一场曾发生在克里克与布拉格之间的剽窃风波。
因为布拉格的禁令,克里克没敢与鲍林讨论DNA。但内心里,克里克更担心鲍林会抢先解决DNA的分子结构。倒是鲍林主动提起他不准备去拜访国王学院,让克里克大松一口气。
三年前,鲍林在英国时只关心蛋白质,没有关顾研究DNA的国王学院。这时,虽然他已经认识到DNA的重要性,但因为曾索取照片被兰德尔和威尔金斯拒绝,他不想再找上门引起尴尬。况且,科里在鲍林无法出国时已经去过国王学院,对富兰克林提供的新照片没有留下特别印象。他倒是向鲍林报告,那里的人员正陷入内斗泥潭,不可能做出实质性的科学成果。
鲍林因而觉得DNA分子结构并不那么紧迫。回到美国后,他一边让科里开始DNA的X射线衍射实验,积累自己的数据,一边继续推广卷曲螺旋,弥补蛋白质结构中剩余的缺陷。但那年11月底,鲍林在一次讲座上看到RNA——DNA的“近亲”核糖核酸——的电子显微镜照片,其中有着圆柱体形状。正如蛋白质的螺旋曾经在佩鲁茨的实验中显现为圆柱体,鲍林猛然醒悟核酸与蛋白质类似,也有着螺旋形结构。这个信息加上阿斯特伯里曾经测得的0.332纳米周期性让鲍林确信他已经有足够的数据如法炮制,像对蛋白质分子一样为DNA分子结构做出大胆的假设。
一个月后,鲍林和科里在1952年12月31日向《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寄出他们的论文。同一天,鲍林给布拉格、兰德尔等众多同事写信,并向英国的《自然》投发快报,预告这一新突破。一时间,鲍林在蛋白质之后又成功求解出核酸分子结构的重大新闻在美国和英国不胫而走。
那正是克里克日日夜夜最为担心的梦魇。
(待续)
inside out
日常的消毒、清洁剂能够“杀死”病毒,就是因为它们可以破坏病毒的蛋白质外壳。
No, we work with our heads.
Waring blender
The House Un-American Activities Committee
A Campaign to Disarm and Defeat the United States
Presidential Medal of Meri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