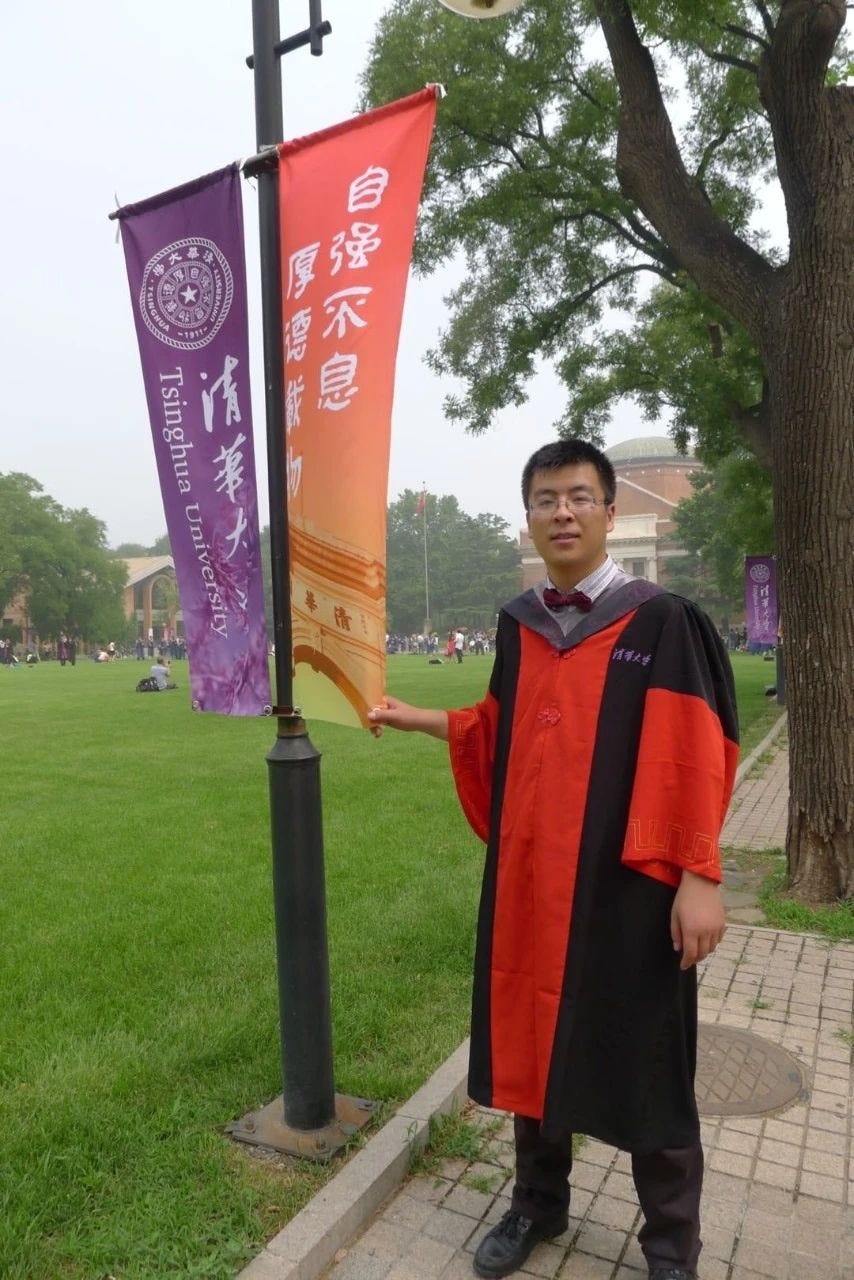生命编码背后的故事(圆二)
偷梁换柱
对疫苗研究的希望和失望最具切身体会的莫过于格雷厄姆。他所在的疫苗研究中心就是一个体现人类面对病毒时决心和挫败的象征。
格雷厄姆身高1米95,是在美国中西部乡村中长大的彪形大汉。他大学毕业后在田纳西州一家医院担任住院医生,同时攻读博士学位。1982年的一天,医院收治一位身上五个不同器官同时在发炎的病人。格雷厄姆竭尽所能也无力回天,后来才知道那是田纳西州的第一位艾滋病患者。这个匪夷所思的病症那时已经在美国各地出现,医生们也都同样地束手无策。
一年后,广州出生、香港长大的美国病毒学家黄以静(Flossie Wong-Staal)终于揭示出这个恶疾的缘由:人类从未见识过的HIV病毒。她再接再厉,两年后又完成病毒的基因测序。有了病毒的生命编码,人类由被动防守转向主动进攻。穆利斯恰在那时发明的聚合酶链反应(PCR)大显身手,为检测病毒提供简单而准确的方法。医学界云开雾散,乐观地认为征服艾滋病的药物和疫苗指日可待。
的确,艾滋病疫苗随后出现。格雷厄姆积极投入临床试验,却发现该疫苗不仅没能阻止病毒侵袭,反而加剧被接种者感染艾滋病的风险。这个失败为满怀期望的医学界及大众带来沉重打击。艾滋病疫苗的研究一蹶不振。
其实,在天花、脊髓灰质炎等传染病中取得非凡成就后,曾经热火朝天的疫苗领域在20世纪后期业已停滞不前。与需要长期服用的药物不同,理想的疫苗往往毕其功于一役,每人只需接种一次即终身受惠。这是疫苗特有的优势,却也对研制公司的盈利极为不利。发明、检验和推广新疫苗需要耗费多年的心血和上亿美元的投资,经常只以无效告终。如果出现艾滋病疫苗那样适得其反的事故,研制方还需要承担责任风险。这些因素促使实力雄厚的医药大公司纷纷撤离这个吃力不讨好的市场。
面对这个尴尬局面,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所属的国家过敏和传染病研究所1主任福奇(Anthony Fauci)在1996年向克林顿总统提议组建专门的政府机构以保障艾滋病疫苗研制的继续。疫苗研究中心在2000年正式开张时,福奇亲自点将由格雷厄姆出任负责疫苗临床试验的副主任。
那时人类认识HIV病毒的生命编码已经有15年之久。艾滋病有了鸡尾酒疗法,疫苗却还是遥遥无期。
虽然艾滋病是疫苗研究中心的首要目标,格雷厄姆感觉HIV病毒可能过于狡猾,人类一时难以取胜。因为病毒早在人类出现之前已经练就一整套卓越的生存技能。
在细菌有了CRISPR免疫系统后,病毒赖以生存的就是自身生命编码的变异,不断地以新面孔骗过细菌墨守成规的CRISPR数据库。病毒的编码储存在RNA分子里,其不稳定的特性正好方便基因随时发生突变。艾滋病的HIV病毒的目标正是人体的免疫系统,也是在通过不断的“变脸”躲过抗体的狙击。HIV病毒的编码常常因人而异,有时即使在同一个病人身体里也会有所不同。正是为了对付这个“多样性”,何大一不得不祭出兴师动众的鸡尾酒疗法,同时在各个环节阻止病毒在人体内的复制。面对如此变化多端的病毒,疫苗也显得无能为力。
好在HIV病毒只是一个特例。人类遭遇的其它病毒不需要以这么极端的方式生存。格雷厄姆认为那才是新型疫苗的突破口。他到疫苗研究中心走马上任之前特意得到福奇许可,在本职工作之余继续研究艾滋病以外的其它传染病,尤其是他作为博士论文课题的“呼吸道合胞病毒”(respiratory syncytial virus,简称“RSV”)。那是一种与麻疹(measles)是近亲的呼吸道传染病,常见于新生婴儿。
麻疹和呼吸道合胞病毒在1960年代后期都有了疫苗,结果却大相径庭。麻疹疫苗行之有效。接种呼吸道合胞病毒疫苗的孩子中很多不仅照样染病,而且病情显著加重。其中还有两人死亡。那以后,呼吸道合胞病毒让疫苗业界避之不及。这个病症继续逍遥法外,每年造成25万人的死亡。
格雷厄姆对有些疫苗不仅于事无补,还常常助桀为虐的表现十分惊异。他在博士论文中系统地重新分析呼吸道合胞病毒疫苗试验时保存的血样,发现该疫苗的确在病人体内制造出针对病毒的抗体,只是其中百分之八十以上没有效用。病毒来袭时,免疫系统忙于制造无用的抗体顾此失彼,为病毒提供可乘之机。而这些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抗体堆积在病人的肺部和呼吸道,也加重了病情。
来到疫苗研究中心后,格雷厄姆还念念不忘呼吸道合胞病毒疫苗这个奇怪的表现。抗体与病毒的结合依赖于“一把钥匙开一把锁”的特异性。无效的抗体可能来自免疫系统为病毒这把锁配钥匙时发生失误。要证明这一猜想,他必须考察病毒和抗体分子的外在形状。因为疫苗研究中心没有这个能力,格雷厄姆只得静候时机。
2008年时,疫苗研究中心新来一位名叫麦克莱伦(Jason McLellan)的博士后。他导师的实验室过于拥挤,让他在格雷厄姆实验室临时凑合。这个安排正中格雷厄姆的下怀。麦克莱伦的专长是结构生物学。那是布拉格父子、威尔金斯、富兰克林等前辈开创的生物学分支,曾经在解析DNA、RNA和病毒的三维结构中大显身手。于是,格雷厄姆抓住机会说服麦克莱伦用他的X射线衍射仪器一窥呼吸道合胞病毒和相应抗体的形状。
呼吸道合胞病毒也有一个外壳,上面有向外突出的蛋白质。因为其功能是与细胞膜上的受体蛋白质相连,促使病毒外壳和细胞膜中的脂质体融合,它们被直接称做“融合蛋白”(fusion protein)。在细致地准备样品和测量分析之后,麦克莱伦发现融合蛋白在与细胞膜融合前后其实有着两个不同的形状。它们因而不是形状一成不变的钥匙,倒像是手指关节可以弯曲的手掌。在接触细胞之前,融合蛋白看起来像是一个握紧的拳头。与细胞融合之后,它华丽转身,变为一只伸直的手指。
这是病毒另一形式的“变脸”。病毒的生命编码没有改变,只是其用作钥匙的蛋白质分子利用自身结构的灵活性改变形状,也成功逃避灭活疫苗制造的抗体。以灭活病毒制作的疫苗中的融合蛋白质绝大多数处于融合后状态,接种该疫苗后的人体免疫系统也就为之准备相应的抗体。但这些为伸直手指量身定做的手掌不能套上握紧的拳头,因而无法抵御病毒的侵袭。为了在病毒接近细胞之前实施拦截,抗体应该针对拳头状的病毒外形制作。
格雷厄姆领悟到这是疫苗成败的关键所在。即使是无需灭活病毒的mRNA疫苗,它们利用病毒生命编码在人体细胞内产生的融合蛋白结构也会同样地不稳定,如同一个关节灵活的手掌一会儿是拳头一会儿是指头。人体免疫系统面对的因而是一个时刻在移动的靶子,无法始终如一地制作有效抗体。疫苗如若成功,用作靶子的融合蛋白必须被锁定在拳头形状上。
于是,格雷厄姆和麦克莱伦效仿当年鲍林分析蛋白质中氨基酸长链结构的手法,细致地考量融合蛋白中各个氨基酸分子的大小和化学键强度,找出其中机动灵活的关节所在。他们发现如果将这样关节附近的氨基酸分子替换为另外稍微不同的氨基酸,就能够像建筑师换用更为结实的材料一样固定那个关节。蛋白质分子也会随之被锁定,不再能改变形状。这个操作在基因工程时代并不困难,只要在融合蛋白的碱基序列中做几个相应的碱基替换即可。
这样,在卡里科真假尿嘧啶核苷的移花接木之后,格雷厄姆和麦克莱伦又找出一个能大举提高mRNA疫苗效用的偷梁换柱手法。与三年前的沃伦和罗西一样,麦克莱伦和格雷厄姆的论文被《科学》评为2013年最佳科学突破之一。
麦克莱伦在疫苗研究中心完成博士后工作后顺利地找到大学助理教授职位。格雷厄姆建议他研究冠状病毒。同为呼吸道病毒,冠状病毒与呼吸道合胞病毒可能有共同的遗传渊源。也许他们的修改手法也能同样地适用冠状病毒。
因为危害不大,冠状病毒是学术界的冷门。但在中国的萨斯疫情过去短短几年后,这个病毒又以中东呼吸综合症的形式再度现身,致死率超越当年的萨斯。格雷厄姆直觉不能继续对这个病毒掉以轻心。无巧不巧,麦克莱伦新招收的一位博士后也对冠状病毒不能忘怀。那是来自中国的王年爽(Nianshuang Wang)。
王年爽比贺建奎小两岁,有着十分相似的成长经历。王年爽出生于山东省贫困农村,通过高考进入青岛的中国海洋生命学院。2009年毕业后,他被保送到清华大学攻读研究生。因为萨斯的记忆,冠状病毒在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备受关注。王年爽的专业也是结构生物学,在中东呼吸综合症出现不久即率先解析其病毒的尖刺蛋白结构。博士毕业后,他申请到麦克莱伦实验室的博士后职位,来美国学习格雷厄姆和麦克莱伦研制mRNA新型疫苗的技术,对付萨斯和中东呼吸综合症的罪魁祸首冠状病毒。
同为病毒的“手掌”,冠状病毒的尖刺蛋白与呼吸道合胞病毒的融合蛋白有着同样地不稳定性,在与细胞膜融合前后展现不同的形状。但二者的结构又相差很大,无法照搬格雷厄姆和麦克莱伦的偷梁换柱手法。王年爽在麦克莱伦实验室里花了一年多时间才找到锁定尖刺蛋白的诀窍:尖刺蛋白中的活动关节在于赖氨酸和缬氨酸在氨基酸长链中的相邻出现。只要将这两个相邻的氨基酸都换成有着更强化学键的脯氨酸,就能锁定尖刺蛋白的形状。他把这个手法命名为“S-2P”设计。其中“S”代表尖刺(Spike)蛋白,“2P”则表示在其中置换两个脯氨酸(P)分子。
王年爽兴奋无比。他们立即写就论文投稿《自然》杂志,不料《自然》的编辑认为这一发现意义不大,当即退稿。在接下来的一年里,他们持续向其它一流期刊投稿,也还是屡屡遭拒。直到2017年,他们的论文才在《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问世,没有引起任何反响。
那时,王年爽和麦克莱伦已经顺利完成动物试验,证明经过S-2P偷梁换柱和卡里科真假尿嘧啶核苷移花接木后的疫苗在老鼠体内产生应对中东呼吸综合症的有效抗体。下一步应该就是实战的人体试验,但他们为时已晚。与萨斯疫情相似,中东呼吸综合症在造成几百人死亡后很快自行消失,不再有检验疫苗的流行感染环境。在这场突如其来的瘟疫中,他们的疫苗只是一个姗姗来迟的马后炮。
久经沙场的格雷厄姆没有失望。他见识过太多来无影去无踪的短期流行病。因为季节、人类生活习惯变化和免疫力等因素,很多猝不及防的流行病只有一年左右的流行期。它们在那期间造成巨大健康、生命和经济损失,疫苗行业却只能袖手旁观。灭活疫苗的设计、试验和制作是一个为时十多年甚至几十年的漫长过程。历史上只有1960年代的腮腺炎(mumps)疫苗只用四年时间完成,但那只是一个绝无仅有的特例。这样的研制周期可以应付天花那种长久存在的病毒,但在萨斯、中东呼吸综合症这一类短期流行病面前不可能有所作为。
但从萨斯到中东呼吸综合症,格雷厄姆也看到这些短期流行病的破坏能力越来越强,不容继续被忽视。这是他在疫苗研究中心处心积虑的大难题。要让疫苗在短期流行病中发挥作用,人类必须从消极等待的被动转变为主动出击,在病毒尚未出现时预先做好准备。一旦病毒现身便能够立即快速反应,设计、生产并推广具有针对性的新疫苗。格雷厄姆知道新型的mRNA疫苗可以在这里大显身手。指点麦克莱伦去研究没人关心的冠状病毒也正是他全盘计划的一部分。
人类面对的已知病毒多达120多种,按照其遗传渊源可以分为25个“家族”(family)。萨斯和中东呼吸综合症发生于不同的时间和不同的地域,其症状和危害能力也不尽相同。然而二者的病毒属于同一个家族,即冠状病毒。它们有着同样的圆球形外壳和王冠式的尖刺蛋白质,其分子结构、形状和编码大同小异。王年爽在中东呼吸综合症病毒中发现的S-2P设计可以应用于冠状病毒家族的所有其它变种,包括在未来出现的未知冠状病毒,最多只需要做些细节上的调整。
格雷厄姆和麦克莱伦在呼吸道合胞病毒上发现的偷梁换柱手法亦是如此,可以适用于那个家族的所有病毒。那时,病毒的25个家族中只有13个有应对的疫苗。冠状病毒不在其列。格雷厄姆的计划是在另外12个家族的每一个选取一种“样板”病原体2,如同冠状病毒的中东呼吸综合症病毒进行研究,像王年爽和麦克莱伦那样找出其中灵活关节所在和相应的偷梁换柱手法。这样,未来出现的任何新病毒都能够根据其生命编码查找已知的锁定蛋白质形状手段,以最快速度完成新疫苗的设计。
所以,王年爽和麦克莱伦并没有白费力气。他们已经为将来会出现的冠状病毒预先准备好疫苗的设计蓝图。
设计只是制作疫苗的第一步。新疫苗的应用还会面临试验、大规模生产和推广等步骤,其中每一步都可能经年累月。格雷厄姆为此绞尽脑汁,力求充分利用mRNA疫苗的独特优势缩短每个步骤所需的时间。
在不屑一顾的宾夕法尼亚大学教授们面前,卡里科曾经一再坚持mRNA分子的不稳定并不是一个弱点。作为疫苗使用时,mRNA不会进入细胞核干预其中的DNA,不具引起体内基因突变的风险。它们寿命很短,在细胞中完成制作蛋白质使命后很快降解消失,也就不会留下永久性的烙印。因此在理论上,mRNA疫苗的风险比传统灭活疫苗低得多,可以相应地缩短人体试验的时间要求。
传统的灭活疫苗需要有大量的病毒以供灭活使用。病毒不是独立生命,无法自我复制。业界通常采用受过精的胚胎鸡蛋作为宿主细胞让病毒侵袭、繁殖,然后通过灭活、分离、纯化、配制等一系列工序生产疫苗。这个生产周期既昂贵又缓慢,本身就需要至少半年。格雷厄姆梦寐以求的“快速反应”因而与疫苗无缘。新型的mRNA疫苗没有病毒成分,其中的mRNA片段可以通过基因工程快速并大规模生产。
这是一个革命性的新思维。但除了偷梁换柱的设计研究,格雷厄姆的“快速反应”战略不过是纸上谈兵。他的疫苗研究中心只是一个研究机构,没有实际的试验和生产能力。在生物技术领域叱咤风云的大公司都因为回报和时间的风险裹足不前,不愿意再蹚疫苗的浑水。格雷厄姆只好寻求更具商业冒险精神的创业型小公司合作。2015年时,他在为王年爽和麦克莱伦的中东呼吸综合症疫苗寻求制造商时找到了莫德纳,意外地发现自己的想法竟与这个不知名的小公司不谋而合。
由生物学家罗西和兰格协同风险投资方创建的莫德纳那时已经有了五年的历史。头三年,他们热火朝天地研制基因治疗药品,结果一事无成。其后,他们在黄翊群的启发下转向mRNA疫苗,也没预料到这个领域困难重重,也没能开发出可以上市的产品。公司的名声随之一落千丈,以至于被怀疑为打着新技术幌子攮取投资的骗局。
面对越来越尖锐的质疑和批评,莫德纳的总裁班塞尔(Stephane Bancel)矢志不渝。他固执地大举投资建造生产mRNA疫苗需要的厂房设备,为公司尚未开发出的产品做好准备。莫德纳的技术人员也下功夫优化脂质体材料,提高其作为mRNA护航者的效率。至于最为关键的mRNA疫苗本身,班塞尔自知公司缺乏专业人才,遂与疫苗研究中心达成协议,为格雷厄姆的疫苗提供生产资源。这是一个两全其美的合作。他们在2017年有了第一个果实,即王年爽设计的中东呼吸综合症疫苗。只不过那是一个迟到的哑炮,让班塞尔和王年爽等人真切地体会到时间在疫苗研发中的重要性和风险。
但他们和都没有灰心。格雷厄姆尤其看重莫德纳已有的生产能力,与疫苗研究中心的科研实力正是理想的互补。在没有新病毒出现的2019年,格雷厄姆提议他们合作举办一次近乎“真刀真枪”的演习,由疫苗研究中心提供模拟的新mRNA疫苗,在莫德纳投入生产,测试从病毒冒头到疫苗上市所需的最短时间。演习的结果将为人类如何应付下一场瘟疫提供最为可靠的数据。
演习预定在2020年初举行。当那年元旦到来之时,一切已经准备就绪。
那却是一个不同寻常的元旦。武汉出现“病毒性肺炎”的消息传来时,格雷厄姆即刻预感那会是冠状病毒的再现。他们准备好的演习正可以直接使用这个新病毒,不需要人为的模拟。他立即给在滑雪场度假的麦克莱伦打电话。麦克莱伦又即刻通知博士后王年爽和一位名叫瓦普(Daniel Wrapp)的研究生。他们这个小队伍在短短几小时内召集完毕,随时待命。
但那时他们还只能等待。格雷厄姆和其他美国卫生官员都无法从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获取病毒的基本数据。直到1月10日的深夜,格雷厄姆才猛然在网站上看到复旦大学张永振教授公开的病毒数据。那正是他们翘首以待的病毒生命编码。
从那一时刻开始,格雷厄姆计划的演习正式启动。
张永振提供的是病毒的全部碱基序列,其中含有16个基因。格雷厄姆他们需要的只是其中的一个:编码尖刺蛋白的基因。那是一个有着3819个碱基的基因,编码着1273个氨基酸。瓦普立即看出这个基因似曾相识,与萨斯病毒的尖刺蛋白基因相比有着超过百分之八十的重复率。瓦普因而信心倍增。他熟练地运用编辑工具在这个基因中实施卡里科的真假尿嘧啶核苷移花接木和王年爽的S-2P偷梁换柱,几乎没费什么功夫就完成了“修改过的RNA”疫苗设计。
格雷厄姆随后又仔细分析这个基因的细节,凭经验添加一些调整。王年爽则花了整个周末的时间细心地该基因切割拆散成六个基因片段。他们需要将自己设计的碱基序列送往中国一家名为金斯瑞生物科技公司3的服务商,由他们合成为实际的样品。王年爽意识到张永振公开发布数据后,世界各地的生物化学实验室可能都会同时在下同样的订单,金斯瑞势必无法及时满足需求。他也知道金斯瑞会优先合成比较小的基因片段。他拆开的基因片段因而会在金斯瑞捷足先登,可能省略长达几星期的等待。毕竟,时间是这场演习中最为关键的度量。
他们没意识到演习将迅速地转变为真实的救死扶伤。
(待续)
National Institute of Allergy and Infectious Diseases
prototype pathogen
GenScript